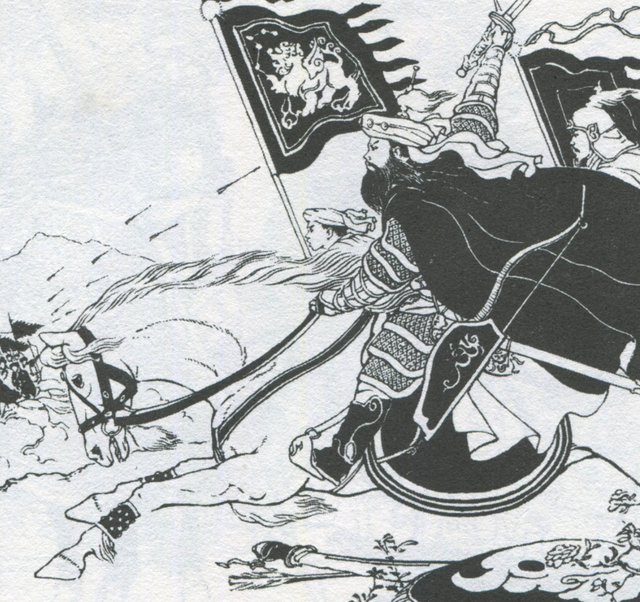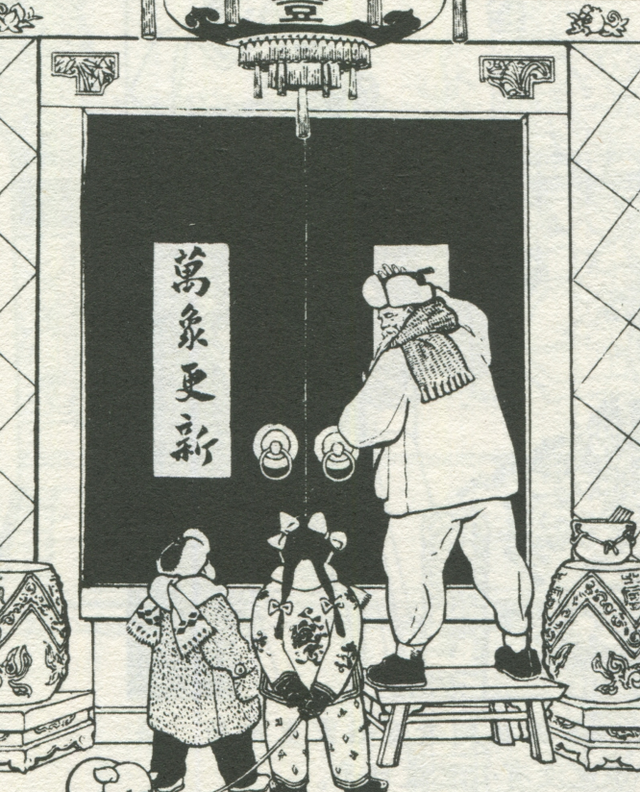1874年3月, 日本橫濱市吉田橋大街上有個西方老人正在悠然漫步。他名叫爵柯蔔·馬克得諾,是從舊金山來的美國漁船“浪浦勒”號的船主。
街上人群熙攘,摩肩擦背。從前面的一個人圈子裏,不斷傳來呐喊聲。
爵柯蔔擠進人圈,原來是兩個壯漢在輪番毆打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周圍的人們大聲喊著:“阿衣喏殼!阿衣喏殼!”
爵柯蔔問了近旁的一個西方人,才弄懂“阿衣喏殼”是日語“混血兒”的意思。混血兒難道不是人! ”爵柯蔔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猛一拳就把一個凶漢擊出老遠。另一個凶漢拔出匕首就猛撲上來。
爵柯蔔躲過那凶漢的匕首,順勢一腳,又把他蹬翻在地。圍觀的人一陣哄笑,兩個凶漢狼狽鼠竄而去。爵柯蔔拉過少年,撫愛地問: “他們是怎麽打你的,不要緊吧?”
少年擦擦嘴角的血,用英語說: “我不讓他們汙辱我。”爵柯蔔同情地問: “你叫啥名字,現在是讓我送你回家,還是送你去醫院?”
少年說他名叫富吉。他主人就是個醫生,住在僑居地39號公館,于是爵柯蔔雇來東洋車,陪送少年到他主人家。
少年的主人是美國人,名叫黑浜。他對爵柯蔔的仗義行爲表示敬意,爵柯蔔謙遜地說: “這算不了一回事…………”
黑浜醫生感慨地說: “由于門戶開放,西方人擁進日本,這就出現了混血兒,而這些無辜的孩子卻遭到淩辱。富吉是我五年前領養的,我希望他能有新的生活。”
爵柯蔔告辭了。醫生熱情地送至門外: “有空請常來玩,看看富吉。” “如果不離開橫濱,我一定來。再見了,黑浜醫生,富吉。”
時近黃昏,海風料峭,海浪有節奏地擊拍著堤岸,爵柯蔔邊走邊 想,他從富吉的遭遇回憶起自己苦難的童年…………
爵柯蔔的父親是美國西海岸俄勒岡州河口一家皮毛公司的英國職員,而他的母親卻是當地的印第安人。他的父親出于生意經,娶了他的母親。
他母親生下他就染病去世。他從小在母親的印第安部落裏生活,學習印第安人原始的狩獵技藝,一直到9歲…………
父親再婚,娶了一個愛爾蘭女人。他失去母親的溫暖,一再逃回那幼年生活過的印第安部落。
父親爲了他的前途,把他送到加拿大,進了一所專爲英國人辦的學校。但就因爲他是個混血兒,而被老師、同學所歧視,常常受到他們的戲弄。
爵柯蔔忍受不了屈辱,就逃出學校,輾轉流浪于加拿大、阿拉斯加州和墨西哥之間。做過牧童,也當過武器走私商的小夥計。
19歲那年,他上了捕鯨船,在白令海上充當水手。不幸,捕鯨船觸了冰山沉沒了。他被愛斯基摩人救起。愛斯基摩人的熱忱,融化了他心頭的冰塊。
整整五年,他和愛斯基摩人一起生活,一同忍饑挨餓。他不但能又適應艱苦的環境,還提高了狩獵技藝,兼備了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的特長。
他以一個技術高超的射手資格,被俄國人開設在錫特卡的皮毛公司所雇用。
他射擊百發百中,任何海獸在他的槍口下都無法逃遁。這使他贏得了好名聲, “混血兒”不再成爲一面精神枷鎖。
在錫特卡,爵柯蔔結識了舊金山的美國皮毛商齊布羅克。他離開了俄國公司,在美國的海獸捕獵船上大顯身手。
光陰荏苒,海水的鹽霜染白了他的頭發,海風吹皺了他的皮膚。這次他指揮海獸捕獵船從舊金山來到這裏,准備在日本北方和俄國千島群島一帶偷獵海獺。
由于珍貴的海獺已瀕臨絕迹,俄國的千島群島和日本的擇捉島雖然還有大量存在,可這兩個國家嚴禁偷捕,該怎麽辦? …………他一擡頭,已經來到了碼頭。
爵柯蔔在積極做出航准備和搜集情報的空隙中,三天兩頭去拜訪黑浜醫生,看望富吉。他們的友誼越來越親密。
有一天,爵柯蔔帶著富吉在碼頭上散步,講述著大海和海員的艱苦生活。正在休息的碼頭搬運工,指著富吉齊聲高喊: “阿衣喏殼!阿衣喏殼!”
富吉漲紅著臉: “我跟他們拼了!”爵柯蔔緊緊抓住他的手,深沉地說: “要沉住氣,我…………我也是混血兒,我理解你的痛苦…………”
“您……您也是 ”富吉撲進他的懷裏。爵柯蔔說: “是的,我父親是英國人,母親卻是印第安人。我與你一樣,是混血兒。面對淩辱,要學會忍耐。懂嗎?”
過了幾天,爵柯蔔又去拜訪黑浜醫生,發現富吉滿臉傷痕。醫生說:“富吉應該離開這個充滿歧視的地方,讓他到船上做個實習水手吧,他不會給您丟臉的!”
爵柯蔔終于收留下富吉,在一個陰晦的早晨,帶他上了“浪浦勒”號,頂風逆浪,沿著日本島向北航行。
船劇烈地顛簸著。富吉躺在吊床上,爵柯蔔手提油燈問道: “嘔吐得受不了吧?”富吉擡起頭決然地說: “先生,我能頂住。”
過了幾天,水手長呼列查怒氣沖沖跑來對爵柯蔔說: “那小子目無上司,竟敢回手。”爵柯蔔心裏明白,他嚴肅地告訴水手長說: “以後別再辱罵他!”
爲了維護船上的紀律,船長茄克杜以反抗上司的罪,處罰富吉在桅杆頂的瞭望台上過一夜。寒冷折磨著少年,他一聲不吭,堅強地忍受著嚴厲的處罰。
船上的人全都改變了對這少年的看法,啧啧稱贊。第二天,當富吉從桅頂上下來時,水手長呼列查親切地對他說“別生我的氣,你這了不起的小家夥。”
幾天後, “浪浦勒”號通過了襟裳岬海面,向第一個目的地擇捉島中部的單寇灣前進。瞭望哨大喊“陸地!”人們看到蓋滿白雪的單寇山出現在左舷前方。
當船通過單寇灣南面灣口時,瞭望哨又大喊: “左舷前方停泊著一艘二桅帆船!”爵柯蔔大聲命令:“查看一下船名!”“瑪麗雅…………阿來托卡,好像是艘俄國船!”
“浪浦勒”號漸漸靠近那船。那邊有人問: “餵,你們是美國船吧?”待聽到這邊的回答後又說: “我們是彼特羅·巴甫洛斯克的瑪麗雅·阿來托克號!”

“浪浦勒”號抛了錨。爵柯蔔乘上小艇前去了解一下情況,看見 一個黑頭發、黑胡子,穿著熊皮大衣的俄國大漢,覺得很面熟,似乎曾在哪兒見過…………
猛然,他記起來了: “真是他! ”此人曾在錫特卡俄國皮毛公司與他共事過。“餵,是依瓦諾夫嗎?”對方用嘶啞的大嗓音回答: “啊,對!爵柯蔔,你的樣子可沒變啊!”
依瓦諾夫緊緊抓住爵柯蔔,大聲喧嚷: “真想念你!我們二十多緊年沒見面了,想不到在這裏巧遇,依舊是同行!”爵柯蔔說: “聽說你殺了人,進了監獄。”
依瓦諾夫彎下龐大的身軀,把鮮紅的大嘴湊近爵柯蔔的耳朵,悄聲說:“我在薩哈林監獄裏忍受了15年,是從那裏逃出來的。”
“我一跑出來,就想方設法重操舊業,可是我那船, ”依瓦諾夫用手朝背面他的船員一指: “那些個破爛夥計,花了整整一個月,才取到5張海獺皮…………”
爵柯蔔知道在這個狡詐的家夥口裏,掏不出更多的消息。依瓦諾夫假惺惺地要留他喝酒,他謝辭了,下了小船,徑自回“浪浦勒”號。
在“浪浦勒”號上,爵柯蔔望見單寇灣內隱隱約約有兩三條密獵船。看來這裏沒多大油水,他下定決心到俄國千島群島附近的得撫島去。
狹長的得撫島海拔1200米,山巒縱橫,自西南向東北傾斜,前端的岩礁一直插進海裏約20公裏,犬牙交錯,是個危險的海域。
瞭望哨忽然發現了海獺群。“浪浦勒”號立即抛錨,放下三只塗了保護色的小艇,每艇有一名射手,兩名劃手,一名舵手。爵柯蔔親自充當射手,指揮小艇前進。
無數的海獺,有的倚伏岩礁上,有的浮遊在海面上。其中有只特別大的雄海獺,全然沒有察覺逼近的危險,正悠閑自得地躺在那密集如床的海藻上…………
爵柯蔔向左右兩艇打了招呼,決定先打那只特別大的。劃手們拼命加快速度,飛濺的海水不斷拍擊著站在艇首的爵柯蔔。
大海獺發現了漸近的小艇,警覺地盯著。爵柯蔔舉起槍,站在搖晃的艇上,首先開了槍,另外兩艘艇緊接著也開了火。
大海獺反複的逃逸並沒有擺脫獵手的槍口,當它再一次浮出海面吸氣時,爵柯蔔的槍響了,大海獺被命中。而棲息在險礁上的其余海獺也是同樣的命運。
這一天,他們獵獲了7頭海獺。獵獲物被吊上甲板,留在船上的人一下子爆發出歡呼聲。
富吉好奇地抓起海獺,爵柯蔔說:“在俄國,5張皮可換一艘小帆船。可是它很難打,即使高明的射手,而且配上優秀的劃手、舵手也得花費不少子彈才能擊中它。”
“浪浦勒”號在得撫島獵獲了42頭海獺之後,便起錨北上。富吉已習慣了海上生活。爵柯蔔看著少年,心想:該教他射擊了,也許他會成爲好射手…………
8月中旬, “浪浦勒”號航行到千島群島的斯萊特尼哈島的5個岩礁附近,被濃霧困住了。爵柯蔔忽然問船長: “你嗅到腥氣了嗎?”船長說: “是的,我也嗅到了!”
爵柯蔔向船頭的人大喊: “餵,前面望見了什麽嗎?”話音未落,只聽“嗵”的一聲撞擊,船身劇烈地震動了一下,傾斜著,並大幅度地搖晃著…………
船長與爵柯蔔不約而同想著是撞上了流冰塊…………船頭水手長呼烈查大聲叫著:“是鯨魚!我在船頭附近看見了它黑色的魚身。”
船長茄克杜腰結纜繩,下去檢查,不久就上來報告:“船主,船頭3米處被鯨魚撞開一個口子,即使開足水泵排水,也只能維持五天。”
五天?”爵柯蔔說: “那就是說必須在五天內趕到設備齊全的港口去修理。”船長說: “是的,但不能去俄國的堪察加和日本的函館,只能去室蘭!”
爵柯蔔查看海圖,事情只能這樣安排。他猶豫了一下,告訴船長: “不能浪費漁獵期。船你開去修理,我帶射手和劃手上岸,你在9月中、下旬回來接我們…………”
“浪浦勒”號在南返修理途中,把爵柯蔔他們載回得撫島。爵柯蔔挑選了包括富吉在內的九個人,分乘兩艘小艇,在西北岸一個無名小灣登陸。
無名小灣的背面是舒緩的斜坡。他們就在斜坡上用漂來的木頭和帆布支起一個小屋,安居下來。
清早,爵柯蔔率夥伴們出獵去了。富吉留在營地拾柴、燒飯,一有空就去小溪裏捉魚。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再沒有以前在橫濱遭受的那種屈辱,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島。
傍晚,人們回來了,圍坐在小屋裏,剝著獵獲物的皮毛,喝著富吉做的魚湯,嬉笑著…………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打發過去。
轉眼到了9月底,氣溫驟降,冰雪就要來了。“浪浦勒”號仍未出現。人們失望地作了各種猜測。爵柯蔔則深信患難與共的茄克杜船長一定會來接他們…………
一直到10月下旬,才看見那朝思夕盼的“浪浦勒”號白色的船體,出現在灣口湛藍的大海上。大家歡呼著,迫不及待地乘上獵艇迎了上去。
艇船相遇了,奇怪的是上面乘坐的不是“浪浦勒”號上的船員,而是那像熊一樣的依瓦諾夫,他說: “你好啊,爵柯蔔,又見面了!”
依瓦諾夫打了個手勢。茄克杜船長被推了出來,他脊背後被人用槍抵住。事情發生得那麽突然,爵柯蔔真後悔沒隨身帶著武器。
“餵,看見了嗎?”依瓦諾夫傲慢地說: “你們敢亂動,首先要了你們船長的命。” “你要幹什麽?”爵柯蔔憤憤地問。“把皮毛交上來,船就更不在話下了。”
爵柯蔔惱怒極了: “畜生,你們這幫海盜!”依瓦諾夫厚顔無恥 地笑著說: “這是沒辦法的呀,老朋友!我的船、皮毛都喪失殆盡,連堪察加都回不去,請多多原諒。”
在槍口的威逼下,爵柯蔔、茄克杜的人除了富吉去島中捉魚之逼外,全被反綁著,抛在沙灘上,匪徒們徑直地踏過沙灘,走向斜坡上的小屋。
茄克杜對大家說: “我悔不該在返回得撫島途中的風暴裏,救了這夥畜生。”爵柯蔔怒不可遏,但又無可奈何: “船上的夥伴怎樣了?”船長說: “都被關在船艙裏。”
爵柯蔔聽到小屋傳來的怪叫喧鬧聲,想著辛辛苦苦獵獲的127張貴重的皮毛,想到自己和夥伴們將被殺害,真是後悔莫及,但是該怎麽辦呢?
忽然,就在前面10米遠的礁石後面,一個瘦小的身影一閃,富吉從隱蔽處跳了出來。他手裏拿著刀和那支獵槍。“啊,富吉!真是全船人的救命上帝…………”
富吉跑到最近的愛斯基摩人瓦比底身旁,放下槍,用刀把捆綁的繩索迅速割斷。突然,看守人發現了,舉槍就放。“啊——”富吉慘叫一聲,倒下了。
小屋裏的匪徒聞聲紛紛跑了出來。“瓦比底,快! ”爵柯蔔大聲催促。愛斯基摩人用刀迅速割斷綁著他的繩索。
被綁著的夥伴都被瓦比底切斷繩索獲救了,這時匪徒們的子彈呼嘯著從頭頂、身旁飛掠而過。爵柯蔔飛快地撿起富吉丟下的槍,進行還擊。

爵柯蔔這個神槍手,一槍就把看守的匪徒擊倒。其他的匪徒也都逃不出爵柯蔔的槍口。
剩下的三個匪徒分散躲藏在岩礁後面,不停地朝爵柯蔔他們開槍射擊。爵柯蔔焦急極了:他們只有一支槍,一比三,持續下去就麻煩了…………
忽見一個匪徒露出了頭, “砰!”爵柯蔔一槍就把他放倒。另一個匪徒嚇得叫了起來: “不要開槍了,我是美國人,我投降!”他舉著手,從岩礁後面走了出來。
“只剩下一個依瓦諾夫,哪裏去了?”爵柯蔔正想著,一個身影一閃,背海朝斜坡上迅速跑去…………“看你往哪裏跑,慢慢收拾你!”
爵柯蔔跑至富吉身旁。他仰面躺著。茄克杜船長盯著少年的臉:“不行了,爵柯蔔。子彈穿過後心…………”
爵柯蔔悲憤地凝視躺在茄克杜懷裏的富吉說: “茄克杜,你們押 著人質去奪回大船,我找依瓦諾夫去,結果他!”
爵柯蔔提著槍,順斜坡上去,跟蹤依瓦諾夫的足印追去。在一條兩米寬溪流對面的樹枝上,挂著一條布片,下面潮濕的地上,留有依瓦諾夫清晰的皮靴印…………
爵柯蔔警覺地察視四周,發現前方沒有了足印。看來是狡詐的依瓦諾夫想把追捕者引入歧路,應當趕快返回。
爵柯蔔憑著獵人追蹤野獸的豐富經驗,果斷地下溪流,溯水而上。走了90米左右,果然發現右岸上留有新踩的靴印。
“匪徒是繞個圈朝海岬方向奔去的。”爵柯蔔奮力追趕。已能看到海灣的遠處“浪浦勒”號的船體,桅頂上飄著一面紅旗。茄克杜他們已經奪回大船了!
依瓦諾夫想把爵柯蔔引向島的深處,自己溜回“浪浦勒”號。卻不知道“浪浦勒”號已經回到茄克杜的手裏,他正拼命向海灣奔去。
爵柯蔔猜透了依瓦諾夫的鬼主意,像獵捕野獸那樣,悄悄地潛伏 在岩礁後面,耐心地等著他的露面。
夕陽被海水吞沒了,夜幕開始徐徐降下…………突然,岩礁後面有個黑影在晃動。“黑熊出現了!”爵柯蔔緊緊地盯住它。
依瓦諾夫完全想不到,爵柯蔔會這麽長時間地埋伏在岩礁後面。他急匆匆地走下斜坡,忽然, “砰!”一聲清脆的槍響,他搖晃了幾下,慢慢地栽倒了。
浪浦勒”號要返航了,天空中無數海鳥在哀鳴。爵柯蔔抱著富吉 的遺體,淚流滿面地對大家說:“我與他不是父子,卻勝過父子之情。他死了,我們卻獲救了,我們要用對待功勳水手那樣,爲他舉行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