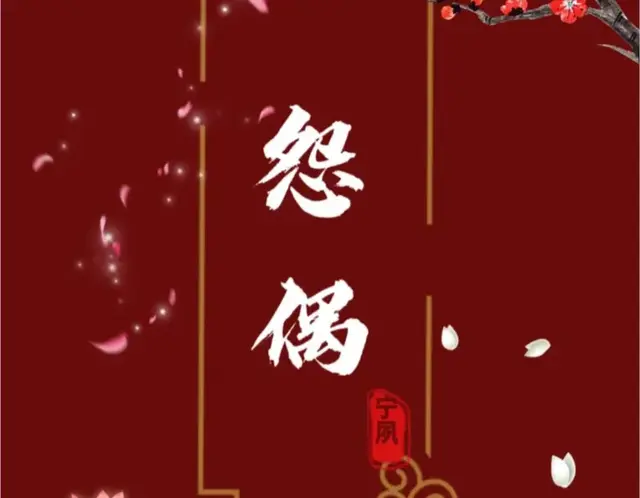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乖前夫黑化了怎麽辦》
作者:綠藥

簡介:
扶薇隱去長公主身份在江南散心時,偶遇一超塵脫俗的郎君,似墜落紅塵的璞玉。她見色起意,使了些手段誘他簽下一紙婚契,婚期一年。契約之婚,卻也琴瑟調和柔情蜜意。
一次意外,她和夫壻那個古怪的雙生弟弟發生了些風花雪月的錯……
傍晚,她指了指唇角,勾清冷哥哥主動吻她。
夜裏,弟弟偷偷覆吻哥哥留下的痕迹,陰暗地瘋狂觊觎。
扶薇以爲自己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可沒想到哥哥和弟弟是一個人???
一年之後,扶薇回京,一向溫潤端方的夫壻立在雨中死死盯著她,狼狽脆弱。
扶薇望著他濕漉的臉,只是笑笑。她說他是一時消遣的樂子,她說京中像他這樣的有千千萬,她還說從未對他真心真情。
後來京中再遇,昔日短暫的乖前夫,成了陰鸷乖戾的新帝。
白璧無瑕的夫壻死在那場淅瀝的雨,陰暗的另一半靈魂占據了他。
于是她被囚在長歡宮。
長歡宮內,他恨聲質問:“你到底喜歡誰?”
“你……你喜歡誰,我就是誰。”
精彩節選:
六月江南,雨膏煙膩。栉比的臨街商鋪籠在朦胧水霧之中。雪腮杏眼的紅裙少女一手護著個牛皮紙袋在胸口,一手提裙,腳步輕盈地穿過長街,翩飛的紅色裙尾在蒙蒙雨霧裏曳過一道亮彩。引得街邊閑散商販直勾勾盯著她,竟是看癡了。直到少女的身影消失在繪雲樓,衆人才回過神。
“也不知道是哪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看呆的路人抿了抿發幹的唇。
“嗤。”蹲在一邊的商販扯嘴笑了,“什麽千金,不過是個丫鬟罷了。”
在水竹縣這樣的小地方,紅裙少女是罕見的美人。可這樣明眸善睐的美人,不過是個婢子。
想到這裏,衆人望向繪雲樓的目光不由多了幾分探究。連婢子都美得不食人間煙火,主子該是怎樣的姑射神人?
靈沼扶著樓梯扶手跑上二樓,探頭一望,沒瞧見人影,腳步不停,哒哒登上三樓。
她推開房門,剛要開口,蘸碧豎起食指抵在唇前,向她輕輕搖頭。坐在另一邊的花影已然皺起眉。
靈沼咬了下舌尖,蹑手蹑腳走進去,將抱了一路的牛皮紙袋輕輕放在桌上。
樓下的商販們若見了蘸碧和花影更是要癡上兩回。不同于靈沼仍稚氣的明燦甜美,蘸碧柳眉鳳眼像仕女圖裏走下來的溫柔佳人,而花影則英氣許多。
內室忽然傳來幾道微弱的咳聲。
這下,三個婢子都皺了眉。
不多時,裏面的咳聲越來越頻密,柔柔碎碎,一聲又一聲,聽得人心焦、心疼。
蘸碧起身,悄聲走到門口往裏瞧,見長公主醒了偎在引枕上咳著。她趕忙轉身倒了溫水,折回門口的時候換了寢鞋,送水進去。
知道主子醒了,靈沼這才小聲給自己辯解:“主子前幾日這個時辰都翻話本呢,我才沒放輕腳步……”
花影橫她一眼,視線又落在桌上的牛皮紙袋上。
靈沼收到提示,趕忙抱起牛皮紙袋走向內室,她還沒進去,先站在門口眯著眼睛笑:“主子,京裏來的信。”
扶薇放下溫水,慢慢擡起眼睛,亦擡起姑射神人真容。
扶薇五官極其豔絕瑰麗,卻被那份骨子裏的高傲壓著,豔而不媚麗而不俗。她半倚著引枕,優雅裏透著高高在上尊貴,如今大病初愈瘦了一大圈,人又不在朝堂之上高坐,少了往日深不可測的淡漠,多了幾許易碎的柔。
世人對美的偏好不同,可沒有人會否認扶薇的天資絕色。一切都是那樣剛剛好,多一分少一厘都造就不了她如此登峰造極的美貌。
扶薇望向靈沼懷裏的東西,潋眸微凝,神色難辨。
蘸碧柔聲勸:“離宮幾個月了,陛下的信寄來幾十封都沒拆過。主子您就拆一封吧?陛下雖完全有獨自理政之能,但以前都是您處理大小國事。眼下您突然放權離京,萬一是陛下在政務上遇到了難處,想要向您征求意見呢?”
蘸碧覺得自己這樣勸不會出錯,因爲長公主向來以國事爲重,這幾年爲陛下、爲國民殚精竭慮。
扶薇卻不爲所動,只淡淡道:“收起來吧。”
蘸碧不再勸了,心裏卻在憂愁長公主和陛下一直這樣僵持著可不行呀。
靈沼已經換了寢鞋進來,踩著柔軟的蠶絲地毯,將牛皮紙袋裏的信收進北窗下雕雲刻鶴的黃梨木箱中。箱子裏,堆了厚厚一摞陛下寄來的信。
這些信都沒有被扶薇拆看過。
靈沼走向床榻,蹲在扶薇足邊仰起臉來,笑出一對小酒窩:“主子要聽曲兒嗎?我給您唱一支?”
扶薇擡眸,瞧著少女特有的朝氣蓬勃,心裏的郁色稍霁。她唇角浮現一抹柔笑,擡手捏了捏靈沼臉蛋上軟乎乎的肉。
“主子笑了就對了!”靈沼笑得更真摯,“來江南就是散心的,管什麽京中的事兒呢?不管不管,就該怎麽開心怎麽來!”
扶薇也覺得靈沼這話說得很對。
“把我昨天翻的話本拿來。”扶薇說著下了床。
靈沼趕忙幫她穿了寢鞋,扶她到南窗前的軟椅坐下。蘸碧已經將扶薇昨天讀了一半的話本放在小幾上,又轉身給她添了一杯溫水。
扶薇以前喜歡喝精致的茶、濃烈的酒、香膩的甜飲子,一切有味兒的東西。但是中毒之後壞了脾胃,如今只喝溫水。
扶薇讓靈沼支起支摘窗,讓窗外的景色泄進來。外面雨已停,潮濕的水霧仿佛還飄在紅塵裏,天地之間朦胧又幹淨。
扶薇望了一會兒窗外,才垂眸將目光落回話本上。蘸碧已將話本打開到扶薇昨天讀停的地方。
這七年,扶薇翻閱最多的是奏折,其次是史冊政律天文地理,根本沒有精力和心情翻閱雜書。此次來江南散心和養病,她想重拾小時候午後坐在樹下看故事書的趣味,可話本翻了幾冊,仍是興致缺缺。
這些蹩腳的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的情情愛愛故事,有什麽可看的?
可她總要換個活法。
貪玩貪吃的黃毛丫頭能培養出掌權執政的能力,如今也能培養出閑散人的心態。
扶薇靜下心來,一字一句地認真看下去。
時間緩慢流走。以前扶薇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如今倒覺得白日夜晚都漫長。
良久,蘸碧估摸著扶薇手邊的水該換了,捧著溫水進來,瞧見扶薇並沒有在看話本,而是望向窗外。已經傍晚了,街市上明顯熱鬧許多。
蘸碧順著扶薇的目光往窗外望去,瞧見那道鬧市中靜坐的白色身影。微怔之後又了然,略思忖,她緩步走至門口柔聲喚:“靈沼?”
“主子有吩咐?”靈沼立刻小跑過來。
蘸碧搖頭,微笑著說道:“你總是往外跑,對水竹縣了解得最多。你知道那個奇怪書生的事情嗎?”
靈沼轉瞬間心領神會,她甜聲:“知道呀!那人叫宿清焉,遠近聞名的大才子。因爲身體不太好一直沒有科舉,讓不少同窗替他惋惜。他經常會來街邊支攤子,替不識字的人寫家書。”
“身體不太好?是有什麽隱疾?”蘸碧追問。
“聽說是有容易昏厥的毛病,不能長途跋涉。而且家中母親身體也不大好,胞弟又常年在外,他就一直留在家鄉不遠行。”
“哦。”蘸碧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扶薇一眼,再問:“家裏除了母親和弟弟還有什麽人?可有什麽作奸犯科的?”
“就三口人,母親和雙生弟弟,身家清白得很。”
“那……可有婚配?”
靈沼遲疑了一下,才說:“他不娶妻的。前幾年有好些主動的姑娘家找媒婆登門說親呢。可他八字太硬,既克母又克妻。他親口說不會成親害人,後來就再沒有媒婆上門了。”
“他母親不是還活著?怎麽克母了?”
靈沼眼睛亮晶晶的,興趣盎然:“本來就八字硬,雙生子雙份八字雙倍硬。只要他們兄弟相見,他們的母親就會大病一場!過年的時候就克了這麽一回,讓他母親躺了兩個月呢!”
外間的花影聽不下去了,冷聲:“都是些什麽神神叨叨的說辭?被人編故事騙了吧?”
靈沼嘻嘻一笑,道:“都是我聽來的。聽來的嘛,必然有真有假。這是蘸碧問,又不是主子問。若是主子問,那才該讓暗衛查個清清楚楚哩。”
蘸碧和靈沼相視一笑,目光若有似無地朝支摘窗旁瞟了一眼。
扶薇望著坐在鬧市中讀書的宿清焉,神色淡淡地抿了一口溫水,令人捉摸不透她的意思。
靈沼和蘸碧當然不可能蠢到在長公主面前隨便議論他人閑事——她們本就是說給扶薇聽的。
這幾日,扶薇窗前翻看話本時經常多看那白衣書生幾眼,甚至隨口誇贊過——“鄉野間竟有這般璞玉之姿。”
能在長公主身邊近身伺候的,自然不會處處都要扶薇吩咐。察言觀色是最基本的能力,只要扶薇一個眼神,她們就會恰當地主動做事。
花影也明白她們兩個的用心,只是花影對她們彎彎繞繞的行事風格嗤之以鼻。她站起身,走到門口,直截了當地說:“主子,您要是看上那書生了,我去將人弄來。一個鄉野書生,能得長公主青睐,是他三生有幸!”
蘸碧蹙眉,給花影使眼色讓她趕快住口。畢竟長公主退婚之事還沒過去多久呢……現在尚且摸不准她的意思。
扶薇卻笑了。
她垂眸,視線睥向手中杯。盞中水面映著她的五官。她纖柔的指端在杯身輕叩一下,水面徐徐漾起,她的五官也跟著浮動。
伴著輕輕一道落盞聲,扶薇道:“出去走走。”
繪雲樓是水竹縣最奢華氣派的酒樓,高高聳立在長街最中央,在一衆平房裏顯得十分令人矚目。于繪雲樓中,不僅能看見近處的熱鬧,也能將整個江南小城的景色納入窗內。貧民百姓鮮少能來這地方,地方官也不可能日日來,是以繪雲樓一年裏大多數沒什麽客人。
可上個月來了位外地的貴人,將整個繪雲樓包下來不說,還嫌髒嫌舊,將樓內重新布置了一番。平日裏只能見到幾個丫鬟外出,那位神秘的貴女幾乎不出門。有那見過扶薇的人將扶薇誇得天花亂墜,信誓旦旦地說她是仙神下凡,引得整個水竹縣的人都對這位美人抓耳撓腮地好奇。
是以,當扶薇邁出繪雲樓,整個熱鬧的長街一刹那寂靜下來,不管是行人還是商販都將目光落在扶薇身上。
一襲龍膽藍的柔紗襦裙裹著她婀娜又挺拔的嬌軀,耀眼的藍襯得她裙上胸口一片欺雪賽玉的白。珠簾面飾挂在鼻梁上遮了下半張臉,是含蓄遮面更是增媚的點綴。
習慣了滿朝文武的跪拜,扶薇對這些灼熱的目光毫不在意,她款步而行,徑直朝著不起眼的代書小攤走去。
所有人都神色各異地打量著扶薇,唯有宿清焉渾然不覺專心讀著手裏的一卷書。
似乎街市的喧囂不入他耳,奇異的安靜也不被他所覺。
靈沼將小杌子擺好,蘸碧將懷裏的軟墊放在其上,扶薇才在宿清焉對面緩緩坐下。
宿清焉視線未離開書頁,聲音清潤詢問:“可是需要代書?”
扶薇有些詫異。原以爲書呆子看書看得入了迷對周圍一切渾然不覺,原來是她猜錯了嗎?
扶薇更細致地打量起面前的書生。于樓上窗前遙遠,只覺他舉手投足間脫俗優雅,與周遭格格不入,似墜落紅塵的璞玉。如今近處端詳,瞧出他更多的昳色。扶薇目光在宿清焉輕垂的眉眼多停留了一會兒,有些驚奇他的眼睫這樣長。她從未見過男子有這樣蜷長濃密的鴉睫。他坐在對面,潤柔安和,歲月靜好。
宿清焉擡起眼睛。
四目相對,扶薇一瞬間撞上一對靜谧幽明的漆眸。平靜、真實,又無暇。這樣一雙眼睛的主人恐怕是個良善到有些天真的人。
這枯燥又漫長的養病散心之旅,似乎找到了點樂子。
扶薇的唇角慢慢漾起一抹笑,貼著臉頰的珠簾跟著晃了一下,在落日余晖的鍍照下,撞出閃爍的璀澤。
“好看。”她忽然說。
“什麽?”宿清焉漆幽的眸中慢慢浮出疑惑。
“先生的字很好看。”扶薇垂眸,視線落在小方桌上的手抄。
字迹清隽,潤如其人。
扶薇收回視線,重新與宿清焉對視,緩聲:“煩請先生代寫一封家書。”
宿清焉不言,直接拿過一張信箋。他一邊研墨,一邊問:“寫給什麽人?”
宿清焉左手執筆,准備妥當將要落字,仍未等到扶薇開口,他擡眸,望向扶薇,安靜地等待著。
寫給什麽人?
宿清焉這個問題把扶薇問住了。她能給誰寫家書呢?和她有血緣關系的家人都死光了,堂表皆不剩。恩重如山的養父母也不在了,留給她一個如今在宮裏當皇帝的弟弟,想起這個弟弟……扶薇心裏就來氣。
“母親。”扶薇念出這個有些遙遠的稱呼。
宿清焉落下這兩字,又等了良久,也沒等到扶薇再開口。他溫聲道:“若姑娘不知怎麽寫,可以告訴我想說什麽事情,在下幫姑娘潤詞。”
“母親應當正因我要成婚而歡喜,可男方家裏既嫌我體弱短命,又怪我強勢出風頭,想要毒害我性命。我該如何告訴母親?”扶薇擡眸,望向宿清焉。
宿清焉望著扶薇眼眸裏的一汪幽潭,愣住。
扶薇慢慢移開了目光,垂眸輕聲:“先生只幫我寫……一切安好,這四字就夠了。”
良久,宿清焉才收回目光,一筆一畫地寫完。
他放下筆,颔首輕吹信箋上的墨迹,直到浮洇的墨汁完全滲進紙張裏。
“姑娘,不管遇到了什麽難事,家人總是會站在你身後,相陪相助。”宿清焉雙手捧上家書。
可是扶薇沒有家人呀。
“多謝先生。”扶薇淺淺一笑,伸手去接。薄薄的一張信箋下,她指尖若有似無地輕輕碰了一下宿清焉的指背,又須臾離去。
扶薇若無其事地垂下眼睛,纖白的指捏著信箋,慢條斯理地將其從當中折了一道。
宿清焉靜靜看著她指上的動作。
扶薇擡眸對他笑了笑,而後扶著蘸碧起身。
走之前,靈沼放下兩枚銅板。
宿清焉看向小方桌上的兩枚銅板。可是……他幫人寫家書向來是不收錢的。
不遠處包子攤的許二等扶薇離去,立刻湊到宿清焉面前。不僅是他,周圍幾個商販和行人也都湊過來,轉瞬間將宿清焉的小方桌團團圍住。
“清焉,離得近看得清,她是不是真的美得跟天仙似的?”許二急忙問。“她下半張臉戴著珠簾是有疤還是歪嘴?或者龅牙?你離得近肯定能看清!”
宿清焉看了許二一眼,再茫然環顧周圍湊過來的一張張看熱鬧的臉龐。
他認真回憶了一下扶薇長什麽樣子,而後緩緩搖頭,認真道:“沒注意。”
濃密的鴉睫下一雙幹淨的眸子將人望著,無辜又真誠。沒有人會懷疑他說假話。
許二一噎,氣得翻了個白眼:“你這個書呆子!”
其他人也一哄而散。
宿清焉的手虛握成拳置于小方桌上,拇指指腹不自覺地貼了一下食指和中指的指背。
他擡眼,望著不遠處的垂柳。夕陽細碎的光粘在隨風拂動的柳條上,仿若貼著嬌靥輕晃的珠簾。
他真的沒注意珠簾之下,他只記得她的眼睛。
宿清焉回頭,人海裏已然看不見扶薇的身影。
扶薇已經回到了繪雲樓。她將信箋隨手放在桌上,擡起手臂,蘸碧習慣性地幫她褪去外衣。扶薇外出歸來第一件事必然是沐浴更衣。
花影早就將沐浴的熱湯備好,扶薇沐浴過後換上舒軟的寢衣,獨自待在寢屋裏。
以前總有處理不完的政務,如今空閑著,扶薇尚不能適應這種無所事事。她呆坐了一會兒,視線落在北窗下那一箱書信。
忽想起蘸碧的話,扶薇忍不住想阿斐會不會真的遇到了什麽難事?
扶薇走過去,終于拆了一封段斐寄來的信。
只看了兩行,扶薇就氣得拂袖。信箋翩翩飄落于地,其上字字句句皆是一顆赤誠之心的款款深情。
扶薇不是陛下親姐姐,陛下也不是太上皇的親子。這事還要從多年前太上皇的一場惡疾說起。那一年向來龍體康健的太上皇突然癱瘓在床,言語也困難,不能處理朝政,只能退位。
可宮中並沒有皇子。
太上皇便從宗親中挑選新帝。許是太上皇寄希望于自己還能再康健,又或者想著日後將皇位還給自己的親生骨肉,太上皇挑選了容西王獨子段斐——段斐當年七歲,剛剛父母雙亡,家裏更是和朝中重臣毫無聯絡。
一個名不正言不順沒有權勢的七歲幼帝,日子有多艱難可想而知。
那一年扶薇也只有十二歲,半大孩子罷了。榮西王夫婦對扶薇有大恩,她一直將段斐當成自己的親弟弟。身爲姐姐,她不得不強撐著,牽著弟弟一步一步往前走。姐弟二人經曆過許多共苦的日子。
段斐被推到這個位子,只能迎難而上,不再有回頭路。她要保護姐弟二人,也要爭一口氣。她希望阿斐長大成爲千古流芳的明君,讓天下不再有戰亂和流民。
心懷希望,縱使熬壞了身子,縱使慘遭歹人毒害差點喪命,扶薇也不曾覺得有什麽大不了。
可她萬萬沒想到弟弟對她的感情過了界,早就不再是姐弟之情。
當段斐抱著她的腿哭著說要丟下皇位和她逃到沒人認識的地方生活時,扶薇直接氣得吐了血。
她氣他這有違綱倫的心思,更氣他不爭氣將皇權天下當成兒戲!
一想到段斐的不爭氣,扶薇又覺得不舒服。一陣反胃,想吐吐不出,最終又變成斷斷續續地咳。這是當初中毒後催吐留下的後遺症了。
蘸碧小跑著進來,給她端來藥。喝了藥過去許久,扶薇才好受些,輾轉睡去。
忙時睡得少沒有精力做夢,扶薇最近倒是常常被夢魇纏著整夜,總夢到小時候逃亡的日子。
第二日傍晚,扶薇又出了門。既是來江南散心,哪有一直待在屋子裏的道理。
她沿著長街緩步,偶爾在某個商鋪或攤販前駐足。不多時,恰好趕上孩童下學,幾個孩童清脆笑著你追我趕往一家茶肆去。他們不是去吃茶的,而是蹲在茶肆外聽說書先生講故事。
“主子。”靈沼壓低聲音,“好像是在說您呢。”
扶薇聽了聽隱隱聽見“長公主”,剛好又走得有些累了,便進了茶肆,找了個僻靜地方坐。靈沼給扶薇在長凳上鋪了軟墊,又從自己帶的水囊裏給扶薇倒了溫水。
“這個長公主是榮西王從外面帶回來的,剛被帶回府,就想爬榮西王的床!”
扶薇笑了。現在對她的編排已經這麽離譜了嗎?她被榮西王帶回家的時候才六歲呢。
“所以說這個和皇家一點血緣關系沒有的女人厲害呢!命好運氣好,自己也有手腕。陛下登基之時年幼,朝野都在猜是平南王奪位,還是兩位丞相主持大局,又或者攝政王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你們猜怎麽著?”
天高皇帝遠,在這偏遠小縣城的人竟能肆無忌憚地議論這些了。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呐!長公主是出了李大人家的門,褲子還沒穿好就往孫大人府上趕。她那宮殿人來人往,文官武將都能去。忙的時候,還要在外面等著……”
扶薇單手托腮,認真地聽著。珠簾下的唇角勾著一抹淡淡的淺笑。
她突然想起好幾年前,她學著史書上說的出宮體察民情,第一次聽見外面的人如何用汙言穢語編排她,接受不了,氣得大哭了一場。
扶薇恍惚那個時候的自己還真是年紀小。她如今再聽這些黃謠,已經渾然不在意了。
“李叔。”宿清焉立在茶肆外,提聲打斷說書人。
說書人正說得起勁兒,給宿清焉使眼色,讓他有什麽事情一會兒再說。
宿清焉就站在扶薇身後,一張長桌之遙。她聽見宿清焉輕歎了一聲。
“李叔,你說的不對。”宿清焉再開口,清潤的聲線越發堅定。
李四海愣住,嘀咕一聲:“又來給我找事兒……”
蹲在茶肆外的孩童們交頭接耳,又好奇地望向宿清焉。
李四海無語,朝著宿清焉走過去。兩個人隔著茶肆的半牆,一裏一外。
“你幹什麽?”李四海質問。
“你說的這些事情沒有根據,都是些添油加醋的謠言。略加斟酌,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李四海無語:“說書講樂子,我又沒說你家女人亂搞?衆人聽個樂子,沒人介意真假。享福的長公主也沒那麽小心眼介意!”
“她介意。”宿清焉認真道。
李四海被宿清焉認真的樣子唬住了。“她介意?她告訴你的?你認識她?人家是長公主,位高權重養尊處優,享了福被百姓議論兩句怎麽了?”
“人非神佛也,皆有喜怒哀樂,怎會不介意?不管她是什麽身份,對是對錯是錯,不該因爲她站在高處就要承受汙蔑。”
李四海頗有幾分氣急敗壞:“那你小子,就能保證我說的全都是錯的?”
“不能。”宿清焉道,“李叔前幾日說到前朝的幾位掌權者或重臣時,講的是建樹功績,而不是這些男女私事。長公主縱使私下混亂,也不該對她的政見成果只字不提,而是一味說些不能確定的荒唐事。”
“李叔,若是私下閑談,晚生絕不置喙。可這些孩子在聽。您對孩子們說這些,不合適。”
宿清焉向後退了一步,深深作了一揖。
李四海望了一眼外面的孩童,氣得胡子都在顫。他指著宿清焉,半天憋出來一句:“怪不得都說你有病!”
李四海轉身,惱聲:“今天不講了!”
一個孩童站在宿清焉身邊仰起小臉,問:“他真的是瞎說的嗎?那先生跟我們講一講長公主吧!”
宿清焉微笑著:“我不認識長公主,不能妄議。”
宿清焉轉身離去。孩童們圍繞著他。——宿清焉有時候會去學堂給孩子們上課,是他們的老師。
聽著那些稚嫩的童聲漸遠,扶薇才慢慢轉過身,若有所思地望著宿清焉如松柏挺拔的背影。
原來這世上還真有這樣的人。如白紙一般的人,欺負起來會有負罪感吧?不過……應當也會很有趣吧?
第二天,扶薇再次出現在宿清焉的代書攤前。
她不坐,宿清焉擡起眼睛仰望著她。
“我這裏有一份繁瑣的差事,只有先生能接手。”扶薇微笑著開口。落日荼蘼的光斑令其珠簾閃爍,不敵她眸色璀然。
扶薇淘來些閑書,有些書年歲長了破舊不堪。她要請一個抄書人,爲她重新謄抄一份。
扶薇說完需求和報酬,等著宿清焉的答複。
宿清焉沉默望著扶薇,半晌才開口:“你識字。”
扶薇坦然回望他,唇畔慢慢漾開柔笑:“我也沒有說過我不識字。先生更沒有說過不給識字之人代書。”
宿清焉想了想,確實如此,就此揭過,道:“我單日要去學堂授書。”
“那雙日靜候先生。”
宿清焉還欲再言,扶薇已經轉身離去。婀娜的身影走進人群,漸遠。
宿清焉剛要收回視線,看見兩個人似乎在跟著扶薇。水竹縣地方不大,互相就算不認識也打過照面。這兩個人遊手好閑,在水竹縣是人人嫌又人人不敢招惹的二流子。
“清焉!”許二又跑到宿清焉面前,擠眉弄眼:“她怎麽一直找你,你們兩個是不是有什麽?”
“沒有。不要這樣說,影響姑娘家的名聲。”宿清焉垂眼,重新將目光落在書頁上讀起書來。
許二摸了摸鼻子,有些無趣,不過又不是第一天認識宿清焉,對他這反應也不算意外。
“對了,昨天你又去找李四海麻煩了?”許二問。
“沒有。”宿清焉否認,“只是說理。”
許二幸災樂禍地笑著說:“昨兒個傍晚,李四海回家的時候,在雙燕胡同被人揍了,四顆門牙都沒了!哈哈,最近都不能去胡謅了……”
宿清焉對這些閑事沒什麽興趣,繼續讀著書卷。待許二走了,他望著滿頁文字慢慢皺了眉。
雙燕胡同?他昨天傍晚好像去了那裏。
宿清焉漆亮的眸中慢慢浮現疑惑。他去雙燕胡同做什麽?那並不是回家的路,甚至是與回家相反的路。
應該是記錯了吧。
他搖了搖頭,繼續心無雜念地讀書。
扶薇沿著長街閑逛了一會兒,在一個賣花的小姑娘前駐足。小姑娘亮著眼睛望著她,試探著小聲問:“姐姐要買花嗎?”
像扶薇這樣的人,一眼看去就和小縣城裏的人不一樣,小縣城裏的人摸不清她的底細,頗有幾分不敢得罪的遠離。
扶薇掃了一眼,隨手一指。蘸碧立刻蹲下來,拿著一方帕子包著花枝遞給扶薇。鮮花離得遠瞧著不錯,可送到眼前了,才瞧見已經有些蔫了。
不過扶薇還是將花買了。
“謝謝姐姐!姐姐你真好看!”小姑娘高興地站起來。
扶薇沒什麽反應,轉身離去。
只是蘸碧多給了小姑娘一塊碎銀。
扶薇如今體力大不如從前,這就要回了。她剛轉身,就看見遠處樹後有人鬼鬼祟祟地朝這邊看。
蘸碧低聲:“跟了一路了。”
扶薇點點頭,早有所料。所謂財不外漏,像她這樣招搖,難免會惹惡人生歹心。
不過扶薇還不至于把幾個地痞當回事。
第二日,宿清焉去學堂給孩童上課。暮色漸染時,他姗姗來遲,在街角擺好小方桌,繼續翻閱未讀完的書。
人群熙熙攘攘,他孑然自處。
天色逐漸黑下去,沿街商鋪一盞盞亮起燈。宿清焉擡頭,望向顯眼的繪雲樓。繪雲樓一片漆黑,沒有掌燈。
雨滴忽然墜落,打濕他珍惜的書。他將書收進牛皮紙袋又仔細藏進懷中,然後慢慢收拾其他東西。雨越下越大,他卻完全不急。在小跑著歸家的人群裏,宿清焉閑庭信步,任雨澆身。
這一場雨下了一整夜,時大時小,天亮時方歇。這一場雨一下子將春送走,江南的夏日突然降臨。枝頭的蟬聲好似在一夜之間變得更加響亮。
午後,宿清焉如約去了繪雲樓。
蘸碧將他領進二樓的書房,微笑道:“先生先坐,我去請我家主子。”
“多謝。”宿清焉道了謝,仰頭望著滿牆的古籍。
書房並不是一間屋子,而是將二樓的大廳改成了書房。一座座書架上擺滿了書籍。尤其是北牆更是整面牆都被書卷填滿。
宿清焉是嗜書之人,立于書海之中,不自覺將呼吸放得輕淺,直到腳步聲敲回他的心神。
宿清焉後知後覺地轉過身。
扶薇一手搭在樓梯扶手上,一手提裙,垂眸踏下一級級樓梯。藍白相疊的紗裙如雲似霧圍繞著她,她整個人仿若也騰雲駕霧而來。走廊盡頭的小窗有熱風灌入,吹起她的裙擺晃動,裙尾下若隱若現一小截光著的腳踝。
幾乎是視線碰到她腳踝的那一瞬間,宿清焉立刻守禮地收回目光。
“先生。”扶薇邁下最後一級樓梯,輕喚了一聲。
宿清焉望過來,看見她沒有戴珠簾半遮的芙蓉面。宿清焉的目光停滯了一息,溫聲問:“哪些書需要謄抄?”
“先生稍等。”
扶薇款步走向一座書架,隨意拿了兩卷書,放在書案上。宿清焉跟過去,立刻研磨謄抄。
一立一坐,扶薇立在書案旁垂眼看他濃密的眼睫。若是撥弄起來不知道是怎樣的觸覺。她的手輕輕搭放在書案上,指端于桌面悄無聲息地撚了一下。
可這樣天真的人,錢權似乎都無用。強囚也沒什麽意思。
宿清焉剛開始抄錄,扶薇捧了一盒香器而來。
宿清焉于文字間擡眸,入眼,是她執著香掃的纖柔玉手。
殘余的香灰被她輕掃,飄起又落下,細密似避不開的紅塵。
“呲”的一聲響,火折子迅速亮起一簇光,也燃起一股香。
扶薇將蓋子放上,一道香從孔洞升出,倔強地筆直而燃。
“抄書枯燥,給先生燃一炷香。”扶薇言罷擡眸,對宿清焉施施然一笑,不等他言,已經轉身而去。
扶薇沒有回樓上,而是拿了卷書坐在窗前的軟椅裏打發時間。
窗外夏日的光將整個書閣照得大亮,纖塵可見在光線下跳躍。
她于窗前而坐,照進屋子裏的大捧日光都先擁過她。宿清焉看向她,她坐在日光裏,好似成了光源。
宿清焉又很快收回目光,專心抄起書。
“啪”的一聲響,是扶薇手裏的書落了地。
宿清焉擡眸,見扶薇不知何時睡著了。
而這卷書的落地聲又將她吵醒。扶薇蹙眉醒來,如畫的眉眼間浮現幾分不悅。天氣突然熱起來,她脊背浮了一層香汗。這份炎熱讓她身體不太舒服。她甚至沒心情顧及宿清焉,徑自回到樓上沐浴。
沐浴之後,仍覺不適,又是一陣幹嘔,喝了藥,她昏昏沉睡去。待她醒來,已經是落日時分。
擺脫不了的糟糕病身,時常讓扶薇情緒低落。
當扶薇走到書閣,微微泛著紫的暮霭灑進屋內,宿清焉坐在暗下去的書案後抄書,一下午沒有起身。
扶薇神情恹恹地立在門口望了他好一會兒,才走向一座書架取了本書。
“換一本書抄吧。”扶薇將書冊放在宿清焉面前。
宿清焉也不多問,直接將書拿過來。將其打開,才發現是本寫滿淫詞豔曲的床笫歡記。
宿清焉不言,拿了本空白冊子,開始抄錄那些不堪入目的詞句。他神色無常,仿佛謄抄的句子和剛剛那本嚴肅的史書並無區別。
扶薇垂眼看著他快要將一頁抄完,才開口:“我是故意接近你的。”
宿清焉習慣性地將一句話寫完才停筆,他擡眼,平靜望向扶薇,道:“我知道。”
扶薇與他直視:“既知爲何不避?”
宿清焉不答反問:“我有什麽可以幫姑娘的嗎?”
扶薇望著他,微微蹙了下眉,默了默,才說:“先生幫我寫一份婚書吧。”
宿清焉因爲她這摸不著頭腦的提議愣了一下,想起上次幫她寫家書時她所言,宿清焉想著興許是和她那門不太好的婚事有關。
他從一旁拿了一張紅紙,問:“新郎和新娘的名諱?”
“先空著。”
宿清焉不多問,將婚書寫完,放下筆,看向扶薇,問:“還抄書嗎?”
扶薇望著他這雙永遠平靜的眼眸,沉默了一會兒,才道:“我抛頭露面經商本就遭家裏人不喜,如今婚事有了變故,又怎敢告知母親讓她憂心。”
宿清焉無意探聽別人的私事,可有人對他傾訴,他會認真地聽。聽著扶薇輕遠的聲線,他眼前浮現扶薇上次說到“一切安好”時的眼睛。
柔情沉靜,藏著故事。
扶薇站得久有些累了,她微微倚靠著長案,垂眸去看書案上的婚書,緩聲:“我想母親來看我的時候,我有夫君在側,琴瑟和鳴。”
宿清焉皺眉。
他剛欲開口,扶薇搶先道:“我身體不太好隨時都可能去世,想來先生是不願意做實克妻之說的。”
“我……”
“又或者先生嫌晦氣,不想沾染重病之人。”扶薇輕輕一聲笑,“一年就好。一年之後我要麽病死要麽離開了這裏。到時候絕不再給你添麻煩。”
她提筆,在婚書上的“攜手一生”的“生”字上劃了一筆,改成“年”字。
宿清焉看著她這舉動,語塞了半天,只無奈吐出一句:“你別胡鬧。”
扶薇轉眸望向他無奈的樣子,終于在他永遠平靜的漆眸裏看出別的情緒來。
扶薇拿起書案上的婚書遞向宿清焉。
“你能幫我的,就是在這婚書上寫下你的名字。”她深深望著他,潋滟的眸中漾起柔情的魅,“宿郎。”
四目相對,宿清焉安靜望著她的眼睛,沒接婚書。
若是小人,這樣的好事必然高興接受。所以有時候和君子打交道還不如和小人做交易。
扶薇輕輕歎息了一聲。
她半垂了眉眼,用帶著幾分憂慮的聲線低語:“之前想過許重金或權勢威壓,可這些應該對宿郎皆無用。宿郎是君子,對待君子只能用別的法子。”
扶薇將婚書放下,開始寬衣。
看著柔絲腰帶纏在她纖細的指上被徐徐扯下,宿清焉才反應過來她在做什麽。他一下子站起身,向後退了一步,狼狽地轉過身去。
“姑娘這是做什麽?”
扶薇瞧著他這反應覺得有趣,先前因病身的低落一掃而空。她饒有趣味打量著宿清焉的神色,手上動作並不停。
衣衫緩緩落地。
她慢悠悠地輕聲慢語:“也不知道用責任要挾,對君子有沒有用呢?”
宿清焉視線落在牆壁上,牆壁上映著兩個人的影子。他的目光不由自主落在扶薇的影子上,他問:“你的下人在哪裏,我去叫她們。”
“避開了。”
扶薇雙手繞到腰後,去扯小衣後脊上的系帶。
她的動作清楚映在牆壁上,宿清焉急聲:“姑娘喜潔,落地的衣裳應該不願撿起再穿。下人既然不在,我可否去姑娘閨房幫你拿衣?”
“你是我什麽人?怎麽能進我的閨房?”
宿清焉語塞,輕歎一口氣,他突然轉身,拿起桌上的筆,在那婚書上行雲流水寫下自己的名字。
扶薇看愣了。
就這?
他這就答應了?她才剛開始逗他啊。
宿清焉放下筆,仍舊不去看扶薇,低著頭道:“姑娘身體不好,如今雖到了夏日,可晚間的風還帶著寒氣。如此之舉若著涼,是給病身雪上加霜。還望姑娘多多愛惜自己的身體。”
扶薇目光複雜地看著這個呆子。
宿清焉輕咳了一聲,再問:“現在能去姑娘的閨房拿衣服了嗎?”
扶薇回過神,道:“門口的櫃子裏就有。”
宿清焉立刻走到櫃子那兒,拿了一件長袍遞給扶薇。扶薇遲疑了一下才伸手去接。她完全不覺得冷,甚至覺得有些熱。可還是將袍子裹在身上。若不然,她懷疑這個呆子不會再擡頭看她。
宿清焉又歎息一聲。他終于擡眼,定定望著扶薇的眼睛:“若姑娘需要,清焉願意相伴。只是希望姑娘不要一時沖動,不能因爲別人的錯誤反而傷害自己。時辰不早,我先走了,姑娘早些休息。”
宿清焉向後退了半步,工工整整地朝著扶薇作了一揖。
扶薇捏著衣袍未系的衣襟,問:“明天過來嗎?”
“明日是單日。”
扶薇輕笑一聲,輕輕的笑柔柔吹入宿清焉耳畔,帶來一陣酥癢。
“那後日來嗎?”
宿清焉垂眼,視線裏是書案上那張婚書鮮紅的一角。
“來。”
扶薇滿意了:“慢走。”
宿清焉轉身,剛走了兩步,忽想起一事,又回過身,遲疑了一下,才開口:“還不知道姑娘名諱。”
“扶薇。”
扶薇拿起書案上的筆,在那張婚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而後提著婚書給他看。
——浮薇。
宿清焉看了一眼她的名字,輕颔首,轉身辭去。
扶薇一直站在原地,聽著宿清焉下樓的腳步聲,直到他的聲音徹底聽不見。
良久,她走到窗口架起窗扇。可外面漆黑一片,並尋不見宿清焉的身影。
而此時的宿清焉已經被蹲守在繪雲樓外的兩個地痞拉進了陰暗的小巷。
“那女人身邊有多少人?錢財都放在哪兒?”
“你不是會寫寫畫畫嗎?現在把繪雲樓裏面的布置畫出來!”
“齊哥,幹脆讓他帶著咱們翻窗進去吧!蹲了那麽久,我已經等不及了!那娘們神神叨叨的,還不是會被咱們降得服服帖帖。”
緊接著又是好些句汙穢之語。
宿清焉皺眉,聽得有些生氣。
另一個人拔出一把匕首,森然的光在夜色裏閃出一抹寒意。他拿著匕首逼近宿清焉,威脅:“你小子老實點,要不然宰了你!”
宿清焉濃密蜷長的眼睫輕輕扇動了一下,他望著匕首的目光裏緩慢浮現一抹好奇。
他若有所思地歪了下頭,清隽如玉的面龐霎那間浮現一個詭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