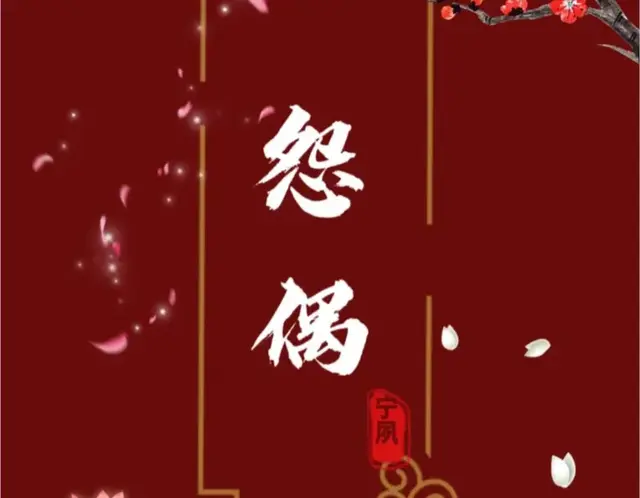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我來京城報仇的》
作者:香草芋圓

簡介:
義父咽氣前,拉著應小滿的手,“抱、抱、抱——”
應小滿含淚抱了抱義父。
義父瞪眼憋氣,含恨擠出最後一個字:“——報仇!”
應小滿收拾包袱來到京城,完成義父遺願,給他老人家……的主人一家報仇。
她要殺京城裏的狗官,晏容時。
京城很大,長得好看的人很多。
某個尋常的下雨天,她救下一個氣息奄奄的男人,長得尤其好看。
好看的男人虛弱地睜開眼,凝視她很久。
他恍惚地說:“皎珠浴光,绯衣染塵。
若輕雲之蔽月,又若流風之回雪……”
應小滿:“聽不懂,說人話。”
男人:“。”
男人改說起了人話,“救命之恩,湧泉相報。
無論姑娘想要什麽,我都能爲姑娘辦下。”
應小滿:“我要殺京城裏的狗官晏容時。”
男人:“。”
得到男人的承諾,應小滿很滿意。“對了,還沒問你叫什麽名字?”
男人說:“晏七。”
應小滿驚了,“你也姓晏?狗官晏容時和你什麽關系?”
晏七面不改色,“狗官晏容時和我住同個屋檐下。我們雖是同宗遠親,卻有血海深仇。姑娘殺得好!”
應小滿驚歎,“京城裏的大家族真複雜啊。”
……
很久之後,應小滿才意外得知。
晏氏掌家的年輕家主,大理寺少卿晏容時……行七。
精彩節選:
天光亮起時,銅鑼巷的積水還沒退盡。
家家戶戶拿盆子往外潑水。應小滿家的賃屋在巷子裏頭,地勢偏高,情況還好一些。巷口有淹得厲害的人家,一家老小在屋瓦上蹲了整夜。
滿屋子漂出去的鍋碗盆勺別指望了,人平安就是萬幸。
還好早上雨勢逐漸停下。蒙蒙亮的天邊現出魚鱗雲,今天或許能轉晴。
義母抱著積水泡透的兩床被子,應小滿踩著梯子往屋頂上攤開,指望出太陽能曬一曬。
院子裏泥濘到無處落腳,義母抱怨,“當初三百文賃下銅鑼巷的屋子,還以爲咱們占了便宜。唉……活該這裏便宜。”
說話間,視線不經意轉到緊閉的西屋,立刻被蛇蟄似地轉開。
“說起來,昨夜你拖回來的那東西……”
義母以“東西”兩字含糊帶過:
“你還真往家裏搬!幸好夜裏沒詐屍。咱們跟他無冤無仇,他死了還敲咱家的門,今天趁天光亮堂把他趕緊送義莊,盡快入土爲安罷。停在家裏,我心裏瘆得慌。”
昨夜受了驚,油燈掉進水裏熄滅,應小滿黑燈瞎火地摸索,把隨著水勢撞門的浮屍磕磕碰碰順著積水拖進屋,放在西屋炕上。西屋的門關上就再沒打開過。
但應小滿敢把屍體拖進屋裏,自有她的打算。
“先不急著送義莊。我昨夜瞧著像是淹水新死的,說不定……”說不定這兩天家人會一路沿著河道尋過來。能順利送還屍首的話,必定會得一筆不薄的酬謝金。
但這麽打算,屍身在家裏不定要停個幾天,義母只怕不答應。應小滿有點犯難。
正躊躇如何說通自家老娘時,遠處又響起一陣細細的哭聲。
哭聲斷斷續續,仿佛失了母貓的幼貓兒,嘶啞得聽不清。
有人砰砰地敲門。對面楊嬸子的嗓門高喊,“應家嫂子!”
義母把被褥往上遞給應小滿,轉身開門,兩人在院門邊議論好一陣,義母心酸地抹了下眼角,回身在竈上摸索片刻,捧出兩個熱蒸餅,硬塞給楊嬸子。
楊嬸子抹著淚把蒸餅收進竹籃裏,又去砰砰砰敲另一家鄰居的門。
“怎麽了?”應小滿坐在屋瓦上看得清楚。
“真是造孽。”義母唏噓,“斜對門徐家的寡婦昨夜沒了。聽說被水沖走一床新被子,徐嫂子心急火燎地蹚水去撈,又不舍得燈油,黑燈瞎火地在門檻邊絆了一跤,摔在水裏沒爬起來就……她家早沒了男人,跟我們家一樣立的女戶。如今娘又走了,剩下個小女娃怎麽活?”
應小滿踩著木梯下來。經過放錢的吊籃時,義母叮囑她,“拿一貫錢下來。街坊鄰居家裏出事,出點份子應該的。待會兒帶錢去徐家看看。”
“哎。”應小滿伸手把細繩紮好的整貫錢撈在手裏。
屋裏到處都是退水後的泥濘,兩人仔細地清掃地面,義母不住地歎息,“好好在自家裏住著,誰想到會發大水淹進門?如今還死了人,造孽啊。”
視線不經意又轉到緊閉的西屋,義母眼皮子再度劇烈一跳。
“剛才話沒說完。西屋這個你還想留著?昨夜運氣好沒詐屍,誰知道今夜會出什麽狀況。趁白天陽氣重,趕緊叫人拉個車送義莊——”
兩人才提起西屋停的屍身,西屋裏突然砰地一聲響動。
義母驚得手一抖,“什麽動、動靜!”
應小滿三兩步擋去前頭,把鐵門栓提在手裏,謹慎推開西屋門。
屍體依舊穿昨夜那身濕透的單衣,從仰面躺著的姿勢變成面朝下的掙紮姿態,一只蒼白的手搭在炕邊。
義母隔門一眼瞧見,頓時驚得面無人色,“詐……詐屍……”
應小滿臉色同樣有點發白。但她畢竟從小跟義父進山,鳥獸屍體見得多了,年輕少畏,提著門栓進門,砰地把門反關起。
隔門高喊一聲,“我把西屋門反闩了。哪怕是詐屍,新死的法力有限,又和我們無冤無仇,我和它鬥一鬥。娘在外頭聽著動靜。動靜不對的話,你別管我,跑出去尋鄉鄰幫忙。”
義母驚得細微發抖,牙齒咯咯戰栗,扶著桌子側耳聽半日,屋內靜悄悄的,什麽動靜都沒有。
……這就更可怕了。
“小滿,裏頭到底怎麽了。你、你說句話啊。”
西屋門打開了。
應小滿腳步虛浮,目光發直,人幾乎是飄出來的。
她恍惚地走去屋檐下,麻木地扯動繩索,降下吊籃。麻木地把吊籃裏剩下的一貫錢提起,揣在懷裏往門外走。
義母惶喊,“去哪兒!”
應小滿: “請郎中。”
“請郎中做什麽!”義母大急,“我又沒發眩暈!那貫錢是咱們娘兒倆整個月的飯食錢!”
應小滿捏著家裏僅剩的飯食錢,目光裏也帶出點茫然。
事情急轉直下,大出意料之外。她混亂中著實想不通——
原本好好的偏財路子,水裏撈屍,等家人尋找過來,把屍身完好送回,得一筆不菲的酬謝金……穩賺不賠的生意,怎麽變成這樣了呢。
“娘,必須請郎中。”
她恍惚地說,“昨夜撈回來的屍體……他還在喘氣。”
……
郎中當然是平時相識的李郎中。
“昨夜發水時,從水裏救起的活人?” 李郎中連連搖頭,“不是我說,這等來曆不明之人,是個大麻煩。”
屋裏不是閨女就是寡婦,李郎中只得自己拿布巾坐在炕邊,擦幹淨“屍身”面孔,再擦拭水草般糾結成一團的烏黑長發。
“人死在水裏倒好,直接報上官府,拉去義莊了事。你們瞧瞧現在半死不活的樣子。”
郎中邊擦邊歎氣,“高熱不褪,肺裏嗆水,身上多處淤傷,左手手背一個血窟窿,瞧著好生可怖,興許牽扯進謀殺命案。人活著進你們家門,如果又死在你們家裏,必定要引來官差問話。搞不好把你們孤兒寡婦家都牽扯進去。”
義母聽著聽著,嘴唇哆嗦起來,“昨夜才拖進來,我們現在就把他扔出去——”
郎中眼皮子一陣狂跳, “那老夫豈不是謀害共犯,不行不行!”
應小滿的想法倒是簡單得很,“那就想辦法救活了。等把人醫好之後,勞煩郎中給我們家做個見證。”
“醫者父母心,當然盡力救治。”郎中眼皮子突突地跳,感覺自己似乎踩進個泥坑,“但治病抓藥,可不是嘴上說說的小事。救人也不是靠嘴上說說救人。”
“應家嫂子也在,老夫給你娘兒倆個當面把話說清楚,四百文是出診費和今天的藥錢。以後再抓藥錢可得另算。治不治?”
應家母女倆互看一眼,齊齊沉默了。
滿屋安靜裏,只有炕上受傷高熱的病人昏迷中微弱急促的呼吸聲。
應小滿開口和阿娘商量,“四百文,也就幾天的賣魚錢,能換回一條人命。娘,治罷。”
“四百文我們出得起。” 義母歎氣,“但你沒聽郎中說?以後再抓藥錢可得另算。誰知道還要出多少?這可是個無底洞。救個素不相識的人……”
“談不上無底洞,每天多殺幾條魚的事。娘,治罷。”
郎中畢竟久居京城,在義母的遲疑神色裏出言指點:
“我看這位郎君身上的單衣是上好綢緞質地,雖說血汙了一大片,賣不出價錢,但家境出身應是不錯。昨夜他漂來時,身上有沒有其他值錢物件?簪子、扇墜子、玉佩之類,哪怕綢緞袍子也能換個兩貫錢。”
應小滿搖頭,“什麽也沒有。”
水流從河道倒灌入陸地,衣裳鞋襪俱沖走,身上還能留件蔽體單衣,是他運氣好。
郎中扼腕惋惜,轉眼又有個主意。
“既然是家境不錯的好人家出身,人不見了,多半有家人四處搜尋。這兩天你多出去打聽打聽,最近有沒有失蹤案子。你若能順利尋到家人,把活人交過去,嗨呀,少不得有重謝酬金。”
“那是!活人比死人值錢多了。”應小滿恍然贊歎,“郎中你懂得真多。”
李郎中老臉一紅,咳了聲,起身告辭。
應小滿把人送出門時,遠遠地瞧見徐寡婦家門外圍住層層圈圈的人,各個露出唏噓神色。有個眼熟的牙婆正在奮力擠開人群,“讓讓,讓讓!讓我瞧瞧這家小丫頭,可憐見的。”
徐家小丫頭還不到四歲,人已經哭啞了,木呆呆地跪在門邊,徐寡婦的屍身橫在院子裏。
牙婆一雙三角眼斜觑女童的臉蛋,從上到下挑挑揀揀地刮一遍,嘴裏念叨:
“這場天災禍事!徐家沒了大人,只剩個不頂事的女娃子,她娘的屍身還擺在地上,有沒有鄉鄰願意出錢買棺木做法事?沒有?老婆子手裏倒是有點閑錢,可以幫忙做一場頂好的法事,讓人安安心心地去。但徐家小丫頭我可領走了……”
應小滿只覺得腦袋嗡地一聲,直接把人扒拉到旁邊去,帶出來備用的整貫錢全塞進徐家小丫頭手裏,對鄰居們說, “我這裏有錢,不夠做頂好的法事,至少把徐家嬸子的屍身先收斂了,別叫人打小丫頭的主意。”
牙婆嘬著牙花叫苦,“這不是魚市的西施小娘子嗎?這回可跟你家沒關系,小娘子攔我作甚!”
應小滿沒搭理她,沖自家院子方向喊,“娘,幫我把網魚的網子拿過來。”
牙婆哎喲一聲,撥開人群往外跑。
邊跑邊憤憤道,“沒個大人撐門面,三四歲的小丫頭能靠自個兒活幾天?老身好吃好喝養她幾年,養大了,再送去貴人家裏差事輕省地供著,老婆子在做善事!不識好人心!”
應小滿奇道,“徐家嬸子屍首還停在院子裏呢。你把她家女兒賣去做牛馬,還做善事?也不怕徐嬸子半夜敲你家的門!三四歲的女娃好養活得很,大不了一天兩頓來我家裏吃。”
圍觀人群紛紛議論起來。
徐家小丫頭擡起哭腫的眼睛,悄悄看一眼擋在身前的應小滿。
兩只小手攥緊救急的整貫錢。
*
這天傍晚,應小滿果然招呼徐家小丫頭過來用晚食。小丫頭叫阿織,輕手輕腳地進了門,扒完半碗熱騰騰的米粥,人卻不走。
扯著應小滿的衣袖,擡起黑白分明的眼睛,怯生生喊了聲“阿姐。”
又沖義母怯怯喊了聲“嬸娘。”
義母的心都被喊化了,彎腰把阿織抱在手裏,掂了掂分量,回頭跟應小滿歎息,“瘦得跟貓兒似的。比你三四歲時輕多了。”不再提送回徐家的時候,把人抱去炕上睡覺。
炕上的小丫頭翻來覆去幾趟,吃飽喝足,身上暖和,沒多久便睡沉過去。
義母坐在炕邊低頭看紅撲撲的小臉。
人留下了,開始犯愁。
“去看看吊籃。”義母低聲嘀咕,“昨夜拖回來一個,吊籃裏的買菜錢全撒了出去。現在吊籃裏頭只剩百來個銅子兒,夠咱家吃幾天?”
應小滿當真跑出去認認真真翻了回吊籃,“足足還有五百多文呢。咱們家吃個十天八天不成問題。”
義母瞪眼,“十天八天以後呢?吃光喝光出門討飯?”
應小滿:“再久的長命雨也不至于連下半個月。十天八天以後天就晴了,我還去魚市殺魚。有主顧吃魚,咱家就有錢吃飯。”
義母哭笑不得,拿起炕上的針線籃子做起針線活:“你啊,天塌下來你都不愁。我再做點針線活計補貼補貼,咱們娘兒倆總不能真的出門討飯。”
“娘你歇一歇。不差這點。”應小滿把義母的針線籃子挪去旁邊,“剛才郎中也說,我們既然救下個大活人,總有辦法的。”
正好到了郎中叮囑的每隔兩刻鍾冷敷退熱的固定時辰,她起身推開西屋緊閉的門。
炕上的年輕男人沉沉地昏睡著。身上還在發高熱。
或許清晨時曾經短暫地醒來瞬間,做出掙紮動靜,但之後整天再沒見清醒模樣。
臉倒是被李郎中擦幹淨了。在水裏泡得過久而顯得極度蒼白的皮膚,如今在高熱下透出不正常的嫣紅。
應小滿坐在炕邊,換過額頭退熱的冰水帕子,取一把家裏的篦子,把男人半濕半幹的頭發仔仔細細篦一遍。
確實什麽簪子都沒有。脖頸也沒有挂值錢的玉墜子。
她有點失望,但談不上意外。隨手取一截布帶把男人的頭發紮起,提盞油燈到炕邊,仔細端詳他的眉眼輪廓。
人既然昏迷在家裏不能動彈,她打算畫一副畫像隨身帶著。這兩天如果在河邊碰上尋人的親友,當場展示畫像,兩邊容易打交道。
她在燈下湊近打量相貌。
鼻梁挺直,眉鬓濃黑,唇形優美。眼睛……始終閉著。瞧著有點像內雙,不確定。
應小滿心裏默默感慨:京城人口百萬,長得好看的人真的很多啊。水裏漂來的浮屍,拾掇拾掇,居然也像模像樣的。
油燈刺眼的光芒映照下,近處的睫毛驟然動了下。
應小滿提著油燈的手倏然一縮。圓眼微微睜大,目不轉睛地盯著面前顫動的睫毛。
眼簾沒有完全張開。
阖攏的眼睑下,眼珠震顫片刻,眼睑露出一罅縫隙,失去光澤的漆黑瞳孔無意識地顫動幾次。
人又徹底昏睡過去。
積水退去的第三天,順天府衙門終于派來安撫百姓的官員。銅鑼巷每家每戶收到十升米糧,胡椒一捧,細布兩尺,預防瘟疫的藥包三包。賃屋的人家減免一個月月租。
河道邊溺死兩人,銅鑼巷溺死一人,報上官府。
“別跟官差提西屋裏頭的人。”應小滿叮囑阿織,“西屋是個大麻煩。不能說出去。”
阿織懵懵懂懂地點頭。
可不正是個大麻煩。
昏迷多日,高燒不退,偶爾迷迷糊糊地睜眼,對周遭光亮和說話毫無反應,片刻後又睡去。
李郎中過來看說,嗆水是一時症狀,倒春寒天氣泡在冰涼河水裏,引發的風寒和傷口感染才致命。好在人年輕健壯,藥劑發汗驅風邪,拿身體底子硬抗罷!
官府慰民發下的胡椒是稀罕好貨,應小滿仔細包好,提去李郎中家裏,抵平最近的欠賬,又提三包藥回來放竈台邊。
義母喜道,“一次給這許多?郎中願意賒咱們藥?”
“這回不是賒的,是送的。今天平了欠賬,我又跟郎中提起打算搬家的事。郎中過意不去,死活要送咱們幾包藥。” 應小滿道。
經過這次河水倒灌,吃了一場大驚嚇,鑼鼓巷的屋子再便宜也不敢續租,義母幾次提起搬家。
只是搬家除去繁瑣之外,還需一大筆押賃金。義母每日對著空蕩蕩的吊籃歎氣。
應小滿左思右想,要不要把義父臨終前塞給她的五十兩銀拿出來。
義父說這是關鍵時刻才能動用的貴重錢財。
入京報仇成功之後,拿這五十兩銀去京城極出名的大相國寺附近,尋一處叫做“余慶樓”的酒樓,進去找店掌櫃的說,“故人前來歸還五十兩銀。”自會有人領她出京城。
應小滿心裏琢磨著,京城容易討生活,她和阿娘不打算回老家了,也就不需要花錢出京城。雖然報仇八字沒一撇,但眼下搬家就很關鍵,五十兩銀用起來正合適。
屋裏彌漫著濃郁的苦藥味,小火熬煮的中藥炖好。應小滿琢磨著事,心不在焉將烏黑藥汁倒入碗裏,端進西屋。
起先兩天連藥都喝不進,都是拿瓷勺撬開牙關,順著縫隙灌下喉嚨。今天明顯好轉許多,瓷勺輕輕一撬牙關,便主動吞咽起來。
“餵,”應小滿拿油燈在眼前晃上一晃,“你醒了?”
人卻依舊毫無動靜,雙眼緊閉。眼睑下的瞳仁半晌才偶爾轉動一下。顯然昏沉沉地並未完全清醒。
應小滿有些失望,又在意料之中。她邊餵藥邊喃喃地念,
“等下我要出門找新屋子。一切順利的話,一個月內便會搬走。你趕緊醒過來罷,下個月我們搬家時,可沒法帶著你走。”
屋外又是下雨天。她穿戴起鬥笠油衣,跟義母招呼一聲,出門直奔城北而去。
聽上次那家茶博士說,晏家在城北長樂巷。
春雨淅淅瀝瀝,霧籠京城。
接近晌午時,應小滿已經站在綠蔭環繞的長樂巷對面,遠遠地往裏探看。
占據半條街的深宅大院,確實容易找的很。
巷子裏清靜少人,巷口卻是另一幅景象。數十披甲衛士佩刀長槍,肅然駐守,進出俱要嚴查。身穿布衣布鞋的尋常百姓連巷子都進不得。
應小滿遠遠地駐足看了一陣。晏家牆裏盛開的粉色桃枝探出院牆。煙雨蒙蒙,亭台樓閣掩映花枝,在雨裏景致霎是好看。
她熟練地尋斜對面街上開門做生意的茶肆,往躲雨長檐下一站。
和門邊閑著無事做的茶博士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
“晏家出什麽事了?這麽多官兵。”
“誰知道。”茶博士果然接口,“反正自從幾日前,晏家門口就多出許多禁軍把守,出入街巷都要查驗身份,指不定家裏出何等大事。”
應小滿點點頭,“聽說晏家世代做官,祖上出過兩任宰相。”
“那是。第二任的晏相,是現在晏家當家這位的祖父,三十年前的故事喽。如今晏家當家的這位在大理寺任職。年紀輕輕做到四品少卿,誰知道將來會不會又出一位晏相?”
應小滿精神一振,“晏家現在當家這位,算京城高官麽?做官的名聲好不好?”
茶博士哈哈地笑出聲:“小娘子你還真敢問。高官是肯定的,至于名聲麽,不好說。”
應小滿有點懵。“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怎麽叫做不好說?”
“這樣和你說罷。京城裏文武百官,最容易博好名聲的,要算禦史台言官。最容易傳壞名聲的——”茶博士沖晏家宅院努努嘴:
“要數晏家這位當家人現今坐的大理寺位子了。大理寺掌管天下重罪刑名,一年過手成百上千個案子,天底下捧他贊他的當然多,罵他的也絕不少。”
……聽君一席話,還不如不聽。
應小滿聽得腦袋嗡嗡的,京城的茶博士說話一個比一個喜歡拐彎抹角,她半天沒琢磨出這番話到底是在誇晏家人還是在罵晏家人。
對著茶博士含蓄高深的微笑,她只能默默感慨,“京城真複雜啊。”
雨勢漸漸小了,她穿起油衣,繞著晏家大宅遠遠地走過半裏地。
按照茶博士的熱心指點,去尋附近一家名氣大、口碑好的莊宅牙人[1],和牙人細細地說清家中情況,賃屋要求,約好兩日後看房,起身回家。
把今天新得的消息琢磨了一路。
快到銅鑼巷時,腳步驟然一頓。
茶博士嘴裏身居“大理寺高位”的“晏家當家人”,和家門口河道中央曾經停過的兩層官船,官船上方高高挂起“大理寺”三字燈籠,終于被她後知後覺地聯系在一起。
應小滿一驚之下,突然又想起——
牙婆把她拉扯去河邊的當天,正值早晨天光好,船頭居高臨下、仿佛挑揀鮮魚一般打量她的那位貴人,她其實隔著河面看清了相貌的。
看起來二十出頭年紀,神色矜傲淡漠,穿一身華貴的火狐裘,腰間佩劍。
長得倒是人高馬大,相貌堂堂,卻仿佛手腳不能用似的,自個兒紋絲不動地站在船頭,只張嘴使喚人,一個人把身邊十來個小厮婢女使喚得團團轉。
應小滿的腦瓜子飛速轉動起來。
當日早晨站在“大理寺”官船上打量她的那位貴人,難道就是茶博士口中擔任“大理寺高官”的晏家當家人,晏容時?
她在不知情時,已經見過她仇家了!
————
傍晚轉小的牛毛細雨裏,應小滿哼著歌兒踩水歸家。
義母在家裏忙忙碌碌地整理箱籠,聽到進院的輕快踩水步聲,從堂屋瞥來一眼,很快又瞄第二眼。
“今天怎麽了 ,格外地高興。”
“我知道仇家叫什麽名字,住哪裏,長什麽模樣了。”
應小滿高高興興地掰開路邊鋪子剛出爐的熱騰騰的炊餅,分給阿織一半,“娘,我很快就能報仇了。”
義母大吃一驚,“別當著小孩子面說這些!”
抱起阿織去屋裏炕上坐著,義母轉身回來堂屋裏,又悄悄問一句,“確定是惡人?”
應小滿咬著炊餅說,“河邊照過面,看著像惡人!”
遙遠的“報仇”兩字突然變得迫近眉睫,義母心底隱藏的憂慮不安瞬時間升騰上來,聲線都開始顫抖:
“你要怎麽報仇?俗話說,殺人償命。就算是個大惡人,也輪不到你這十幾歲的小娘子動手啊。你爹糊塗!”
“娘別怕。我是剛入京的外地人,和晏家人一個不認識。就像娘說的,誰也想不到我身上。”
應小滿越想越覺得有道理,贊歎說,“我爹真是個明白人。”
義母總覺得哪裏不對,但又說不出具體哪處不對,皺著眉頭做飯去了。
吃用過一碗開胃驅寒的胡辣湯,幫著收拾幹淨桌上,應小滿叼著炊餅坐在桌邊,開始循記憶慢慢地畫像。
義母掃地的間隙湊過來瞧一眼,吃驚問,“你畫的是人還是山貓?方裏帶圓一個腦袋,中間長圓一個鼻子,兩條長線眯縫眼睛,喲,還斜眼看人。”
應小滿放筆細看,自己也不大滿意。她平日裏學畫畫兒,都是對著山上的鳥獸魚蟲畫,沒怎麽畫過人。
指著桌上的“山貓”圖,她嘴裏如此形容:
“這便是我仇家的長相——單眼皮狹長眼睛,小麥膚色,眉毛濃黑,相貌堂堂,眼神陰沉。”
義母琢磨了半日,“聽著確實有些凶惡。像惡人相貌。”
“山貓”圖下頭還藏著另一幅畫兒,義母好奇心起,取來面前迎光細看,頓時就露出想笑又忍笑的模樣:
“這幅又畫得誰?還是方裏帶圓一個腦袋,又黑又亮兩只眼睛,喲,雙眼皮的狐狸。”
應小滿臉皮一紅,把畫兒搶過來,對著“狐狸”圖,嘴裏形容道,
“天庭飽滿,眉毛濃長,膚色白淨,雙眼皮大眼睛。——這個畫的是西屋那位。”
義母奇道,“你怎知西屋那位是大眼睛。人壓根沒醒過,閉著眼。”
“是雙眼皮大眼睛。”應小滿堅持,“短短醒過一瞬,我瞧見了。”
母女兩個正小聲嘀咕時,阿織蹬蹬蹬地跑出來堂屋,驚奇地喊,“阿姐,快過來看。西屋哥哥好像醒了!”
西屋炕上昏沉沉三四日的年輕郎君,人掙紮在清醒和昏昧之間,眼睛似睜似閉,濃黑睫毛時不時地抖一下,眼睑偶爾睜開一條縫隙,便被屋裏亮光刺激地閉上眼去。
義母如臨大敵,急忙把阿織抱回自己屋裏,又把女兒往後拉扯,自己擋在前頭,湊近謹慎問,“這位郎君,你醒了?”
屋裏母女兩個睜大四只眼睛,瞪視良久,榻上的人動也不動。
應小滿失望道,“沒醒。”
話音才落,睫毛連同眼睑又明顯抖動一下。
炕上的男人細微而吃力地點了下頭。
西屋的郎君身體底子好,從連續三日不退的高熱裏硬扛過來,來勢洶洶的一場風寒沒能要了他的命。
但人雖恢複清醒,卻開不了口,輕易挪動不得。
勉強眼睑掀動,露出霧蒙蒙的渙散眼神,乍看一眼周圍便閉起。
想要說幾個字,嘴唇開合,只斷斷續續地發出幾道氣聲,說什麽再聽不清。
應家母女倆才放下的心又提起來。官府發下赈濟的兩尺細布,扯半幅送去郎中家,換來一趟看診。
李郎中登門時,榻上的男人已經再度昏睡過去。
“鬼門關裏逃得一條性命,耗損太大。不著急讓病人說話,命還在已是萬幸。”
“臥床靜養,能睡則睡。每日按時服藥,右手背的傷口早晚敷藥,不要碰水,防止傷口化膿。多吃點補氣血的東西……呃,”李郎中打量幾眼四下裏寒碜的土炕木桌,
“罷了。叫病人臥床靜養,早晚多食些小米粥,亦可調養身體……”
郎中絮絮的叮囑聲中,應小滿盯著窗外檐下的吊籃發呆。
五天了。
之前大理寺官船在河道裏撈出的兩具腐爛屍身,據說果然牽扯兩起謀殺命案,這幾天在京城各處傳得沸沸揚揚,轟動一時。
但深夜順水飄來她家門的這位郎君,竟像沒有家人似的。一個大活人憑空出現,連個水花都未驚起。
她接連五天揣著畫像在河岸邊轉悠,趕來城南河邊尋人尋屍的半個親友都沒撞著。
“……溫補滋陰的小米粥!”郎中放重語氣,“可聽見了?知道你家家境不好,但再敷衍要出人命的。”
應小滿瞬間回神,“聽見了。每天兩頓溫補小米粥。”
看一眼榻上昏沉睡著的消瘦郎君,她的思緒又飄散了。
難道不是京城本地人?或許是外地來京城的商賈,被人在水上謀財害命,謀奪財物,所以才尋不到家人……
尋不到家人,就得不到重金酬謝。還得給他一天兩頓小米粥。
應小滿憂郁地歎口氣。
難怪人人都攔阻她。撈屍這個行當果然不是新手輕易做得的。
——不小心水裏撈出活人,就是賠本生意呐。
郎中興許誤會了她這聲歎氣,目光掃過這間不折不扣的陋室,壓低嗓音慎重叮囑:
“應小娘子,你們自己也新到京城不久,又是女戶。你救他一命足夠,多余的事別牽扯進去。等你們搬家那日,不管這位病情有沒有好利索,讓他自己走。”
炕上平躺的郎君細微地動了下眼睑。
外頭堂屋響起細碎的腳步聲。側耳旁聽的義母坐不住了,起身走去竈台邊翻找。
竈上還有點官府赈濟的米面,夠全家吃兩三日,但熬粥滋補的小米需額外買。家裏昨天才咬牙買回來兩升小米,專門預備著給阿織喝粥長身體的。
義母喃喃地道,“人醒了,又多張嘴。”
應小滿沒吭聲,起身把西屋門虛掩住,從袖管裏取出一把精致折扇,遞到郎中面前。
“李郎中,你見識廣,幫我瞧瞧這把扇子值多少錢。我想去尋個當鋪把扇子當了。”
李郎中接過折扇,在光下定睛細瞧,立時倒抽一口涼氣,“象牙扇!質地細膩無暇,精細镂空雕工!難得的好東西啊。你如何得來的?”
“貴人在路邊送的。”應小滿如實說。
郎中驚詫萬分,“這等好東西,哪有在路邊隨手送人的道理。”
應小滿露出躊躇的神色。
她不是很想回答。
躊躇時不自覺偏了下頭,陽光落在她柔和的眉眼輪廓上,如白瓷無暇,如皎月生光,讓周圍粗陋屋室都生出了光彩。
郎中眼皮子一跳,當即感慨地歎了聲,“應小娘子你的話,被貴人上趕著送好物件,倒不奇怪……哎,老夫倚老賣老勸一句,你心眼實在,別上人的當。送名貴象牙扇給你的貴人心思多半不簡單呐。”
應小滿雖然心眼實在,但人又不傻。
二月裏誤入雁家當天,雁二郎領著她進門,屁股沒坐穩,她正低頭端詳大冷天被硬塞手裏的冰涼涼的扇子,就有管事拿一份新寫好的契書進屋要她按手印。
當時,雁家管事矜持對她道:“二郎看中你是你的福分。這把象牙扇是賜你的,你自己收好。入了我們雁家,錦衣玉食、绫羅綢緞樣樣不缺。二郎尚未娶妻,按規矩不能先納妾,你先在二郎屋裏伺候著,日後少不了擡舉你一場富貴。”
應小滿驟聽到“納妾”“伺候”,頓時感覺不對。吃驚之下起身就走,倒把扇子給忘個幹淨。直到一路打出門去才意識到象牙扇還抓在手裏。
往事曆曆,惹人生氣。
應小滿不想多說,只搖了搖頭。
郎中心裏生出許多猜測,忍不住替眼前這位生得罕見好容色的貧家小娘子擔憂起來,翻來覆去地查看象牙扇,指著末尾扇骨的朱紅小印示意她看:
“象牙扇骨上刻有私章,這把折扇是有主的。輕易莫送進當鋪,當心原主報官把你捉了,說你偷盜貴物。即便你說是原主在路邊送你的,無憑無據,你身上生滿嘴也說不清啊。”
應小滿大爲震驚,難怪那位雁二郎隨手送她。原來報官就能追回去。
她氣惱說,“京城的貴人心眼許多都是壞的。”
“別別別,京城貴人不少,別一棒子全打死喽。”郎中舉起玉扇墜端詳,“這白玉扇墜沒有特殊印記,倒是可以送當鋪,少說能當三兩貫錢,也好解你們家的燃眉之急。”
應小滿轉驚爲喜。兩貫錢也能吃許多天了!
她把象牙扇扔去一邊,扯下白玉扇墜收好,起身送郎中出門。
阿織不知何時進的西屋,她回來時正趴在榻邊,驚奇地喊,“阿姐,他醒了!眼睛開了。”
應小滿坐在炕邊,低頭打量半日,納悶問阿織,“他哪裏醒了?”
阿織急得手腳比劃,“我剛才摔一下,他就醒了。阿姐看,阿姐看!”爲了證實她沒撒謊,阿織的小身體往榻上一撲,原樣又摔在榻上男人的胸口,硬生生壓出一聲悶哼。
應小滿:“……”
應小滿急忙把阿織抱去炕下,俯身湊近看去,昏睡多日的人終于緩緩睜開了眼。
果然是雙眼皮。
一雙天生眼尾微微上挑的漂亮桃花眼,兩只眸子霧蒙蒙的,仿佛浸濕了京城三月的春雨霧氣。
應小滿抱著阿織坐在炕邊,兩人睜大四只烏溜溜的眼,屏息靜氣地等著。等了半晌,人卻始終毫無動靜,只有睜開的眼睛昭顯人已清醒的事實,就這麽定定地望著,也不知能不能看清眼前景象。
良久,應小滿遲疑地左右揮揮手。“看得見麽?”
男人終于眨了下眼。嘴唇開合幾下,吐出的依舊是氣聲。
阿織小跑出屋,捧一盞溫水回來。應小滿把所有門窗都打開,讓屋裏更爲亮堂,將瓷碗遞過去小心餵幾口水,男人劇烈地咳嗽起來。
這回終于能開口說話了。
說話時依舊是半醒未醒的迷茫神色,恍惚地注視著面前的少女,開口也是極細微的沙啞嗓音,“皎……皎……珠……”
應小滿:?
茫然和阿織對視一眼。
應小滿:“交什麽豬?”
手邊的溫水遞過去唇邊,連餵幾口,炕上躺著的郎君迷茫半阖的眼睛閉上又睜開。
眼前的虛幻重影漸漸消失,陽光越過迷霧,映進現世的屋瓦窗桌。
這是一座結構粗陋的磚瓦房,看得出有年頭了。剝落的牆漆被仔細修補過,遺留下深淺斑駁痕迹。
桌椅家具擦拭得幹幹淨淨,俱是多年舊物,短缺一截的桌腿用瓦片墊起,湊合著繼續使用。
陽光從窗戶映進來,映在炕邊坐著的少女和幼童身上。暖色陽光從窗外映照在少女的素衣布裙上,鴉色發尾垂在肩頭,明眸皓齒,朱唇渥丹,象牙色的肌膚仿佛在發光。
昏昧時驚鴻一瞥的殘余印象,他落水之後誤入瑤池仙境,绮年玉貌的仙子涉水而來,將他從水中托起,救下他的性命……
幻覺?他不覺得是幻覺。
男人久久地凝視著眼前人,混亂地想,“昆侖山神女和仙童?不對,神女理應著仙衣……爲何無人供奉神女七彩仙衣……”
應小滿坐近幾分,擔憂地揮了揮手,“你還是看不見我?”
男人渾身一震。
映照在素色衣裳上的陽光,落在他重影的視野裏,憑空添加七彩絢麗顔色。神女素衣沾染豔色,腳踩祥雲翩然而來。
“皎珠……”
滿室安靜,半清醒半迷蒙的郎君恍惚地說:“皎珠浴光,绯衣染塵。若輕雲之蔽月,又若流風之回雪……”
應小滿的眼神裏帶出三分懷疑,七分警惕。
她擡手輕輕地往男人鼻下碰觸一下,困惑地縮回手。
分明在喘氣。是大活人,不是詐屍的水鬼。
大白天的說什麽鬼話呢。
“聽不懂,說人話。”應小滿不客氣地打斷,舀起一勺溫米粥,塞進剛蘇醒的男人嘴裏。
榻上郎君本能地閉嘴嚼了嚼。小米粥寡淡,加了點鹹菜調味,滋味正好。這是百姓家常見的菜式。他外出辦案時,偶爾也吃到幾次類似的農家粥飯。
男人的眼神從迷茫漸漸恢複清醒。
神女斬釘截鐵的六個字外加一口小米粥令他徹底清醒過來,混亂的理智從虛無缥缈的昆侖山外拉回清醒人世。
年輕郎君吃力地擡手。層層包裹紗布的手背往上,擦過應小滿正握著瓷匙的手腕。
觸手溫熱,脈搏鮮活跳動。
不是世外神女,是世間恩人。
應小滿一怔,放下碗勺,“你幹什麽呢?”男人已經挪開手,規規矩矩地放去身邊。
“對不住。”微微上挑的一雙潋滟桃花眼閉了閉,再睜開時漾起了光。
他開口換個說辭,“多謝小娘子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