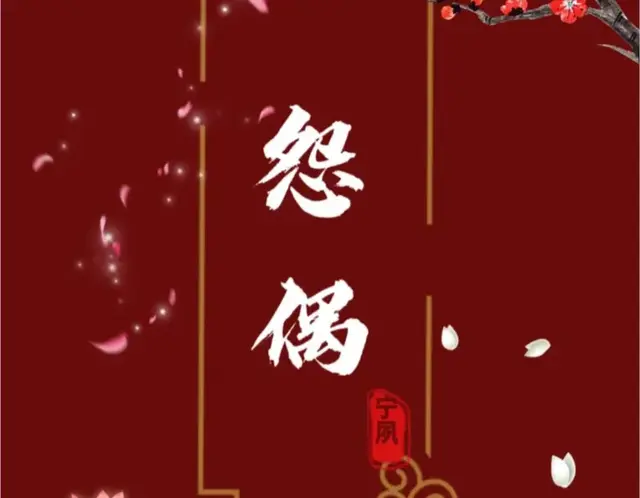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侯門夫妻重生後》
作者:起躍

簡介:
白明霁及笄那年,晏家派媒人上門替世子晏長淩提親,同是武將之後,也算門當戶對,父母一口答應,她也滿意。
十七歲白明霁嫁入晏家,新婚當夜剛被掀開蓋頭,邊關便來了急報,晏長淩作爲少將,奉命出征。
一年後,傳回了死訊。
對于自己前世那位只曾見過一面,便慘死在邊關的夫君,白明霁對他的評價是:空有一身拳腳,白長了一顆腦袋。
重生歸來,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白明霁打算幫他一把,把陷害他的那位友人先解決了。
至于害死自己一家的姨母,她不急,她要鈍刀子割肉,她萬般籌謀,等啊等啊,卻等到了姨母跌入山崖屍骨無存的消息。
白明霁雙目躥火,“哪個混賬東西動的手?!”
晏長淩十六歲時,便上了戰場,手中長矛飲血無數,二十歲又娶了名動京城的白大姑娘,人生美滿,從未想過自己會英年早逝。
枉死不甘,靈魂飄回到了府中,親眼看到自己的結發妻子被人活活毒死。
重生歸來,他打算先履行身爲丈夫的責任,替她解決了姨母。
而自己的仇,他要慢慢來,查出當年真相,揪出那位出賣他的‘摯友’他一番運籌,還未行動,那人竟然先死了。
晏長淩眼冒金星,“誰殺的?”
得知真相,兩人沉默相對,各自暗罵完對方後,雙雙失去了鬥志。
晏長淩:重生的意義在哪兒?
白明霁:重生的意義到底在哪兒?
既然都回來了,總不能再下去,晏長淩先建議,“要不先留個後?”
白明霁同意。
就當晏長淩一心撲在了風花雪月上,自認爲領悟到了重生的意義時,白明霁‘跌’入懸崖的姨母到了白家,昔日背叛他的那位‘友’人,也奇迹般地活了過來。
晏長淩:“......”玩我呢?
小劇場:
窮盡一身本領終于蕩平一切,晏長陵如願摟住了自己的夫人,本以爲今生再也沒有什麽可以阻礙他風花雪月......
半夜突然被踢下床,“你閨女哭了,去哄一下。”
“你那好大兒,又把先生氣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二寫的一手好字,連他自己都不認識了,爲人父,你總得管管。”
晏長陵:曾經有一段清閑人生擺在面前,我沒珍惜......
“晏長陵!”
“來啦——”
精彩節選:
蕭瑟窮秋,日猶長,外層兩道淩花風門大敞,殘霞金光蔓延至階前,似輕煙的光芒裏映照出一層薄薄綠蔭蒼苔來。
已記不清這院子有多久沒來人了。
白明霁面朝庭院,盤腿坐于蒲團上,微擡手,三經絞羅繡花鳥的大袖垂至膝上,手中茶盞傾斜,水漬緩緩浸入金獸爐脊上的細密小孔,眼前筆直的一道袅袅青煙,很快沒了蹤影。
“我與晏侯爺說,歸根結根我不過是外姓人,不該同晏家一道陪葬。”
“他答應了,給了放妻書。”
“姨母,我可以回家了。”
即便孟挽嫁入白家,成爲父親的繼室已有半年,白明霁還是習慣叫她姨母。
她只有一個母親。
便是她的生母,孟錦。
孟挽似乎從不介意,笑著道:“恭喜阿潋。”
丫鬟素商已收拾好東西,在車上等,孟挽沒著急帶她走,新泡了一盞茶,輕推給她,“晏家最後的一盞茶,嘗嘗吧。”
白明霁不擅于悲秋傷懷。
嫁入晏家一年,她從未與夫君晏長陵相處一日,對晏家並無感情,如今要走,沒什麽可留戀。
不僅是晏家,她對任何人或事皆是如此。
從不談感情。
是以,每到抉擇之時,她總能冷靜地找到那條于自己而言,最爲有利的道路。
這樣的性子,彷佛天生。
三歲那年,父親接回了他的青梅竹馬,兩年後,誕下了庶妹,她和母親的處境逐漸艱難。
一個心裏裝著別的女人的丈夫,母親覺得做什麽都無濟于事。
但她認爲並非如此。
這世間能永恒的東西,唯有利益。
她是白家名正言順的嫡長女,母親乃前太傅嫡出長女,父親明媒正娶的夫人,憑什麽要被旁人爭了光芒?
爲了替白家爭光,她使出了渾身解數。
七歲時便能彈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十四歲時,一副丹青被刑部看中,雇她爲官府畫師。
十五歲及笄禮上,她又以無可挑剔的禮儀和一身好皮囊,從此名聲大噪,博得了白太後的贊美和喜歡。
十七歲嫁給了赫赫有名的永甯侯府世子,晏長陵。
她承擔起了白家長女該有的模範榜樣,成爲了白家後輩中最爲出彩的那一個。
她的努力,也如願替她帶來了收獲。
姨娘離開白家那日,父親曾在她屋裏沉默地坐了一柱香,問她:“真不能容她?”
她答:“不能。”
她喜歡自己掌握命運。
瞧不起瞻前顧後的白雲文,討厭遊手好閑的白星南。
看不慣白楚的軟弱無能。
對一頭栽進感情裏的白明槿更是恨鐵不成鋼。
她一直認爲自己才是活得最通透的那一個,直到某一日她回過頭時,身後已尋不出一個認識的人。
如同眼前這條鋪滿了苔藓的台階。
此時來接她回家的大抵也只有姨母一人了。
白明霁垂目,茶盞裏飄浮起了一層青葉,輕輕吹開,送到嘴邊飲了半盞,喚道:“姨母......”
她想問,她到底哪裏做錯了。
察覺出那樣的問題,不是她這樣的人應該問的,終究沒能開口,問道:“阿槿還好嗎。”
白明槿是她的同胞妹妹。
喜歡上了人人唾罵的刑部侍郎裴潺。
一月前兩人大吵一架,至今沒來,怕是還在生她的氣。
“死了。”
孟挽輕淡的聲音入耳,白明霁還未回過神,心口冷不防一股刺痛撕扯而來,似是沒聽清她的話,茫然看向孟挽。
孟挽並不著急,面上是一貫的微笑,“都死了。”
“你母親死了,妹妹也死了,白家老夫人被你寒了心不願再見你,你父親視你爲蛇蠍,護著你的白太後也已薨。”孟挽輕聲問:“阿潋,你離開了晏家又能去哪兒呢?”
門外的金光一點一點地褪去。
震驚與疼痛交織,白明霁疼得額頭冒出冷汗,便也明白了肺腑裏的絞痛是什麽,孟挽今日不是來接她回家的,是來要她命的。
母親死後,待她最親近的人只有這位親姨母,當初爲了助她嫁入白家,自己不惜與父親決裂。
爲何要來害她?
白明霁想不明白,忍著疼痛拽住她,眸子裏血紅如絲,質問道:“爲何?”
孟挽被她拽得斜了身子,沒有回答,而是從身後取出一個漆木盒子放在幾上,打開蓋,輕推到她面前,“你父親給的,讓我帶話給你,你體面了一輩子,最後必然也想走得體面些。”
裏面是一條白淩。
涼意滲進骨頭,肺腑裏的疼痛到了極限,白明霁竟也麻木了。
孟挽傾身過來,五指捏住她的下颚,將她的視線扭向院外,“知道白家爲何沒人來接你嗎?”
白明霁心往下沉,彷佛知道她接下來要說什麽,臉上的血色眼見往下退去。
“因爲他們都厭惡你,恨不得你死。”
孟挽看到了她臉上閃過的一絲慌亂,滿意地松開她,緩緩從她手中抽回衣袖,“你父親身爲兵部尚書,乃三品官階,納個妾卻被自己的女兒鬧得滿城風雨,在世人面前擡不起頭。”
“你大義滅親,帶著大理寺的人上門指認白老夫人陷害了你母親,逼得她從此不敢再踏出房門半步。”
“你氣性高,瞧不起愚鈍之人,白家兩位公子被你踩在腳下,見到你都怕。”
“還有阿槿,就因爲她喜歡的人,你不喜歡,便執意讓她斷絕情愛。”
“知道她怎麽死的嗎?”孟挽輕歎:“我不過是告訴她,以你阿姐的性子,怕是永遠都不會妥協,她的人生容不得瑕疵,也容不得自己的親人有半點瑕疵,不如我來做主,替她許了這門親,昨日親事定下來了,誰知她又自缢了,你說她到底爲何不想活了?”
孟挽掃了一眼她蒼白的臉,目露憐惜,“你以爲是你拯救了白家,可白家上下實則視你爲蛇蠍。你奮力往高處爬,以爲會迎來他們對你的喝彩。”
“你錯了,他們對你只有憎惡,晏家給你了一條活路,你就能活了?”
那一字一句無不刺耳,猶如一把把尖刀刺入心口,不斷絞著她的五髒六腑,尖銳的嗡鳴幾乎刺穿了耳朵,嘴角鮮血湧出來,白明霁擡手抹了一把,滿手粘稠,目光中夾雜著被揭穿後的恐懼和恨意,渾渾噩噩地朝她撲去。
孟挽起身退開,看著她撲在一旁的木幾上,幾面上的一株松柏落下,碎片滿地,無不狼狽。
孟挽又走上前,憐愛地摸著她的頭,似往日那般溫柔地同她道:“阿潋,你沒錯,錯的是他們。”
“我也沒錯。”
“瞧你,每一步都走對了,不一樣落得個舉目無親的下場。”
“潋潋,這樣活著真的幸福嗎?”
那樣的神色充滿了溺愛與憐憫,就像母親死的那一日,孟挽來到靈堂,將她摟進懷裏,對她說,“我知道潋潋心裏苦,潋潋不怕,有姨母在。”
腦袋裏看著跟前這張被水霧模糊的臉,腦袋突然一團混亂,逐漸成了空白,唇瓣輕顫,苦痛地道:“我不知道......”
孟挽一笑,“你知道,很痛。”
“當年你母親也很痛苦。”
“你們下不了手,姨母來幫你們一把。”
淩亂的思緒從混沌中一瞬炸開,白明霁慢慢擡起頭,不可置信地盯著她,喉嚨裏的嗓音幾近嘶啞,“是你殺的母親?”
孟挽不樂意了,“是你們自己走到了絕路,關我何事?”
“你們這樣的人,沒有心,眼中永遠只有利益,下場不是早就注定了?”
“你母親當年同說我,她活得很痛苦。”
“既然痛苦,不如死了,我成全了她......”
孟挽的聲音忽近忽遠,白明霁喘不過氣來。
幸不幸福,她不知道,她未曾有過,並不在乎,但有一樣孟挽說得沒錯,她沒有心,誰都別想從她身上討到好。
鋒利的瓷片劃破掌心,用盡最後的力氣,她將那塊破碎的瓷片刺進孟挽的頸子後,自己也倒在了地上,仰頭往外望去,最後一眼入目,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腹部的疼痛慢慢地變得遲鈍,眼睛一陣陣發黑,耳邊聲音傳來,她已辨不清是孟挽在掙紮,還是從門口灌進來的風聲。
她拼了一輩子。
還是沒能得到善終。
她想保護的人,也一個都不在了。
聖賢人道:盡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她這般孤魂野鬼,應該入不了輪回。
—
昨夜一場驟雨起,狂風卷著悶雷響了半宿,今晨剛住點。
“上月來信,說是走水路,白家的船只都到揚州了,又改成了馬車,這一路上車輪子攆著稀泥走,不存心折騰人......”
一陣細風穿透窗紗,漠漠輕寒拂向臨窗人的臉頰,白明霁扭回頭,便對上了一雙敢怒不敢言的怨怼目光。
說話的人正是白家那位遊手好閑的二公子白星南。
一觸到白明霁的視線,白星南立馬縮了脖子,四下裏一張望,見馬車內就他們兩人,脊背頓時挺直,防備地看著她,“我已滿十五,高你一個頭了,你若再敢以暴力服人,我可要還手了。”
白明霁一笑,“你哪回沒還手?”
“是你不講武德,老揪我頭發。”
“你沒揪?”
白星南不樂意了,“誰有你豁得出去,自小打架回回拼命,非得贏了才算......”
“你倒是拼點命,也不至于連童試都沒過。”
腳下的馬車一頓,應到了城門,白明霁沒再搭理他,拂開窗簾,瞧去窗外。
幾日陰霾後,久違的日頭似水洗過般穿透翠柳,初陽澆枝,葉面殘珠如露,入眼滿目芳華。
當下確乃驚蟄時節。
劇毒斷腸之時,她瞧得清楚,庭外碧雲天,黃葉地,是個窮秋。
雖不可思議,但事實如此,她沒死,幾日前醒來,自己又回到了半年前。
孟挽還未嫁入白家。
今日才進城。
白星南極爲不願跟她走這一趟,“孟氏成過一回親的人了,來我白家是爲大伯續弦,用得著我這白家的二公子來接......要說我,這事壓根兒就不該你管,你已經是晏家少奶奶了,晏長陵不在家,你又不用相夫教子,閑來時養點花花草草,過個輕松日子不好嗎,非要回來鹽吃蘿蔔淡操心......”
白明霁撩起簾子往下跳。
白向南嘴裏嘟嘟囔囔,跟著下了馬車,兩人一前一後走去城門口的茶館。
驚蟄的天氣乍暖還寒,白星南雙手套入袖筒內,一到茶館卯腰便往屋裏鑽,“太冷了,先喝盞熱茶。”進去後沒見人跟進來,又探出個腦袋,喚了一聲,“長姐......”
白明霁已背過身,面朝著城門,婀娜的身姿立在茶館門前的青石階上,青絲垂于身後,腰間處的水藍發帶隨著裙裾迎風飛揚,身影紋絲不動。
“客官,幾位?”
他才不會陪她受凍,白星南轉過頭,“兩盞茶,做好了,給門外那位姑娘送一盞去。”
小二一笑,“好呢,不就是晏家少奶奶嘛,名動京城的白家大娘子,小的認識......”
白明霁等了好幾日,只爲今日。
她要再殺一次孟挽。
好好清算,慢慢殺。
候了半柱香,頭頂的日頭越來越淡,隱約飄起了零星雨點。
聽到身後有腳步聲,白明霁以爲是白星南,待人走到跟前,腳步便主動往對方的傘底下靠了過去。
手肘相碰,一股清淡墨香入鼻,白明霁詫異地轉過頭。
來人並非白星南。
而是大理寺少卿嶽梁。
前世母親死後,爲了證明是被人害死,她不惜挖墳開棺,大半夜跑去嶽府砸門,愣是把嶽梁從被窩裏拉了出來。
尤記得那晚嶽梁站在棺材前,臉色黑如鍋底,後來許是被她纏得沒了脾氣,一來二去,倒也成了半個知己。
前世死之前,才見過他,不算陌生。
冷風刮來,雨點往裏傾斜,嶽梁把傘往她頭頂移了移,側目問:“等人?”
白明霁點頭,“嗯。”
雷雨天,城門口的人並不多,能躲的都進了屋,站在外面的只有他們兩人,莎莎雨聲中嶽梁低聲道:“令堂的案子,白老夫人與白尚書均沒有確切的作案證據。”
母親的死,前世她一直懷疑是祖母和父親所爲,如今既知道了凶手是誰,白明霁便道:“多謝大人,往後母親的案子,不必再查了。”
嶽梁眉宇間正泛出幾絲疑惑,“駕——”城門外突然傳來了一陣馬蹄聲。
兩匹快馬疾馳而來,進了城門,也不見半點減慢的痕迹,很快踏進兩人跟前的水坑,泥水爆開,瞬間四濺,嶽梁一只手握住她半邊肩膀,下意識擋了過去。
白明霁從他懷裏擡頭望去,面色帶著微愠,視線正好與前面那匹馬背上的人對上。
是一張意氣風發的少年臉。
身上和臉上染了些泥水,稱得上狼狽,但那雙眼睛看人時赤|裸張揚,眼底的鋒芒暴露無遺,如同一只從長空直下,俯視而來的鷹隼。
白明霁沒見過此人。
見嶽梁被泥水幾乎澆汙了半邊身子,再看著那揚長而去的馬尾,眉頭蹙起,“粗俗。”
這話引得一旁面色本還怔愣的嶽梁,回過頭來,懷疑地看著她,“你,不認識他?”
白明霁不明白他爲何這麽問。
她應該認識?
沒等嶽梁解釋,城門外又是一陣打馬聲。
這回馬匹還沒到兩人跟前便停了下來。
馬背上的小厮翻身而下,快步走到白明霁跟前,神色慌張,拱手禀報道:“娘子不好了,這幾日落雨,山路濕滑,昨兒半夜,孟娘子的馬車跌入了山崖......”
兩匹快騎疾馳入城,一路揚起泥水,到了鬧市方才減緩。
雖落雨,京城最繁華的前門長街人群依舊熙熙攘攘,周青光夾緊馬肚與前面少年並肩,對適才一幕印象深刻,揚聲調侃道:“沒想到半年過去,京城世風竟如此開放,連嶽少卿這樣的人,也能鐵樹開花,當街與小娘子摟摟抱抱了。”
“少管閑事。”
細雨沾濕了發冠,少年面上的泥土也被沖刷幹淨,膚色白皙,泠泠水漬貼在面上,如同白玉鑲了一層流光。
先前眸中的那道鋒芒早已斂去,寬大的朱紅鬥篷鋪在身後,眉目間的英氣隨著他唇角的舒展,散出幾分渾然天成的傲慢貴態來。
陰霾天裏,乍一瞧,不覺讓人眼前一亮。
少年勒住缰繩,停在一家酒鋪前,從懷裏掏出一粒碎銀,抛向撐開的直棂窗扇內,“兩壇桃花釀,純的。”
雨天鋪子前豎著的一根桅杆上懸著一盞白紗燈籠,陰沉的天光下折射出一圈明黃的光芒,待賣酒的老板看清跟前少年的臉後,驚呼道,“晏世子?”
“前線的仗打完了?”這可是京城裏的名人,酒鋪老板探出大半個頭,擺出一副要與其暢談的熱情,“大宣將士是不是跪地求饒了?”
人人都喜歡聽痛打落水狗的故事,本國將士一旦出征,百姓恨不得敵軍是紙糊成的,一刺就穿,一推就倒。
晏長陵沒應,坐在馬背上半彎下腰,微微上揚的唇瓣勾出一道明朗的笑容,“這酒好賣嗎?”
“小本買賣罷了,還過得去,不敢勞世子費心。”
“安心賣你的酒,家國戰事,也不用你來操心。”說完手中長矛探去鋪子,勾住繩子挑起了兩壇子酒,夾馬繼續往前,直奔侯府。
晏家乃皇室宗親,又因父輩立下過汗馬功勞,門第顯赫,府門乃一扇朱漆將軍門,枋與柱相連,額枋上豎著一塊牌匾。
牌匾上的“晏府”二字,乃晏家老王爺當年親手所寫。
落雨的緣故此時府門緊閉,周青光扣了五六下門環,裏頭才傳來動靜。
見到門外兩人時,門房一臉震驚,懷疑自己看錯了,“世子回來了?!怎的沒提前傳信,奴才這就去通報老爺......”
晏長陵一腳跨入門檻,“不必,父親在哪裏,我自己過去。”
門房快步跟在他身後,“驚蟄天雷雨不停,今日陛下免了早朝,莊子的人趁暴雨前摘了幾框橘子,這會子人都在老夫人院子裏聚著呢......”
晏長陵將手裏的酒壇子遞給了身後的周青光,腳步直徑朝老夫人的梧桐院走去。
七進的院落飛檐連廊,以花格欄杆作裝飾,棂條上雕刻著繁瑣的雲紋和燈籠框紋,一直延綿到正屋門外。
步上廊內,隱隱的說話聲從窗格內滲出,“世襲官職沒了,今後再好的出身,想要入仕都得科考,外頭百姓放著煙花爆竹慶祝,直呼萬歲,我晏家卻被架在了火爐子上被人盯著烤,一句不能依靠祖蔭,害得老二別說實職,在京城連個挂名都撈不到,淪落到了要做地方官的境地,只怕赴任那天,便是全京城最大的笑話......”
官職改革,得有犧牲。
皇室宗親,不愁餓不死,就算什麽都不用做,也能領俸祿過日子。
可之後呢?
便是再也起不來了。
“蔭不及族人,誰還願意繼續賣命......”
“慎言!”
便是在這片刻的安靜中,外屋的丫鬟忽然喚了一聲,“世子爺。”
屋內幾人一愣,齊齊朝簾門望去。
老夫人上了年紀畏寒,三月了屋裏還烤著火盆,晏長淩擡手掀起卷簾,碳火的溫暖馨香撲面而來,與記憶裏那場蕭瑟血腥的畫面截然不同。
“世子?”
“雲橫!”
“你怎麽回來了?”
晏長陵拱手一一見禮,“祖母,父親,二伯二嬸,三嬸......”
進屋前,他已整理了一番儀容,此時對著衆人牽唇一笑,笑出了風光霁月的俊態,可不就是昔日那副招人眼的風流模樣。
還真是世子。
屋內的人終于從驚愕中回過神,爭先問候,屋裏的丫鬟一通忙乎,備座的備座,沏茶的沏茶,晏長陵上前靠著老夫人身側入了座。
等所有人寒暄完,一旁的晏侯爺晏塵阙才皺眉問:“仗打完了?”
“尚未。”晏長陵答得倒是幹脆。
晏侯爺眉頭皺得更深,未等他再開口,老夫人便出聲打斷,“天下的仗能打得完?如今官場動蕩,這時候回來正好......”
半刻不到,府邸上下全都知道了晏家的世子回來的消息,屋裏的小輩們也一窩蜂的湧來了梧桐院。
十幾個高登坐得滿滿當當。
都是熟悉的面孔。
晏長淩掃了一圈,沒見到一個陌生的。
在他這一眼尋望中,晏老夫人也終于想了起來,屋子裏少了一個人,轉頭問:“少奶奶呢?”
邊上的一位丫鬟過來垂目回禀:“今晨一早,說是有要事回白家去了。”
又回白家。
晏二夫人忍不住插話,“能有什麽要事,用得著她天天往娘家跑,世子都回來了,還不去尋?”
自從侯夫人去世後,府上的事務皆是晏二夫人幫襯著老夫人在打理,上回在那新婦跟前吃了個閉門羹後,已好幾個月沒管過,也不知道成什麽樣,轉頭吩咐身旁另一位仆婦,“你去竹院走一趟,盯著人早些把院子收拾出來,好讓世子先回去更衣......”
—
白家。
城外的消息一傳回來,二房的嬷嬷傘都顧不上撐,濕著兩邊肩頭,一踏入屋內便急切地禀報:“二爺二夫人,出事了。”
今日白家上下原本就緊繃著一根弦,一聽這話,白二夫人心跳都快了,“怎麽,真遇上了?”
上月白家大夫人的杖期已過,白家大爺也到了該續弦的時候。
人選定了兩人。
一位是白大夫人的妹妹,也就是白明霁的親姨母,孟挽。
一位則是曾被白明霁親手趕出白家的阮姨娘。
姐姐去了,由妹妹來填房,京城之內的大戶人家並非沒有先例,但耐不住阮姨娘是白大爺心中的遺憾和求而不得。
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牌夫人生死,終于能將受了委屈的舊人重新迎入門,眼裏怎能容得下旁人。
且那孟挽還嫁過人,死了丈夫。
白明霁今日來接孟挽的同時,白大爺也正在迎回阮姨娘的路上。
但孟挽也並非沒有成算。
若白明霁能趕在阮姨娘進門之前,先一步將孟挽接進白家,再去宮中求白太後做主,就算白大爺接回阮姨娘也沒用。
兩廂裏都在較著勁,這要是回來的路途中忽然碰上,會發生什麽,簡直不敢想。
嬷嬷卻道:“孟家娘子的馬車翻了!”
“什麽?!”二夫人驚得站起身來,回頭看向白二爺,兩人均是一怔。
嬷嬷繼續道:“雨天路滑,路不好走,那孟娘子又心急走了近道,馬車翻在了九嶺坡,連人帶車跌進了懸崖......”
白二夫人深吸一口涼氣,好半晌才回過神,“大娘子人呢?”
“倒是立馬趕過去了,還能如何,十幾丈高的山崖,孟娘子已是屍骨無存。”
好端端的人,突然死了。
這就是命啊。
二夫人捏著絹帕,又慢慢地坐了回去。
白二爺皺著眉,思忖片刻,起身便往外走。
白二夫人一把將他拉住,“你去哪兒?”
“人都出事了,總得去瞧瞧。”
白二夫人更不能讓他走了,“人沒了,你去瞧有何用?本就是他們父女間的較量,你摻和進去,站誰?一個幫的不好,裏外都不是人......”回頭吩咐嬷嬷,“把門關上,就說二爺昨兒個喝多了,我看顧著。”
等到白明霁從城門趕回來,整個白府已是鴉雀無聲。
別說主子了,偌大的院子連個仆人都看不見。
白星南躲在了她十步之外,恨不得也能遁了,聽說孟挽出了事後,他大氣都不敢出,被白明霁拖著去了一趟城外,親眼看到了馬車翻滾的痕迹後,更是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自己這位長姐從小要強,想做的事沒有一件不如願,頭一回見她失利,還是栽了這麽大一個跟頭,可謂是滿盤皆輸。
要她那樣傲嬌的人,對著昔日被自己趕出去的姨娘叫母親......
白星南打了個寒顫,不敢往下想。
偷偷窺了她一眼,見其面色緊繃,著實不敢招惹,趕緊差身旁小厮去傳人,很快小厮回來了,頭垂到了胸口,“老夫人頭疼犯了,還在歇著呢。”
“父親母親呢?”
“二爺昨夜喝了一宿的酒,早上才回來,二夫人正在伺候湯藥......”
白星南不死心,又問:“大公子呢?”
“在屋裏懸,懸梁椎骨。”
白星南:......
平時讀書怎沒見他如此用功。
本還想問二娘子白明槿呢,及時想起來,半月前,因她私自外出去看刑部裴潺,被身旁這位長姐禁了足,還在關著禁閉。
合著丟了他一人在這兒受死。
欲哭無淚地扭過頭,眼裏那抹生不如死突然被一雙清透的眸子捕捉到,白星南心頭一跳,便聽白明霁問:“我很可怕?”
白星南腿都軟了,“長姐,我向你保證,就算大伯明兒真把阮姨娘接回來,我這輩子也不會承認她身份,更不會叫她一聲伯母......”
白明霁沒說話,唇角努力動了動,“沒事。”這幾日她已經盡量在笑了,“你回屋吧。”
話音一落,白星南腳底如同抹了油。
那弓腰駝背的樣,毫無半點志氣可言,心緒忽然一陣翻湧,‘廢物’二字在腦中破土而出,白明霁眼睫輕顫,一口氣從城門外憋在了如今,唇角壓了又揚,揚了又壓,起伏幾回,終究還是暴露了情緒的波動。
“站住。”白明霁忽然道。
白星南脊背一僵。
“你去同他們傳個話,門既然要關,就關得結實點,別不該開的時候他又打開了,那樣會讓我覺得是在故意針對我。”周圍更安靜了,白明霁掃了一眼角落裏露出來的幾方衣角,淡聲道:“既知道我脾氣不好,就別招惹。”
好好說話,見人就笑,不好意思,她真不是那塊料。
縱然這輩子依舊舉目無親,不得好死,她也改不了了,就這樣吧,破罐子破摔,總算舒坦了,轉過身跨出門檻,也不用勉強擠出笑容,煩躁的心緒索性挂在了臉上,想不明白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孟挽死了。
與前世完全不一樣,不覺讓她懷疑,這醒來的人生到底還是不是上輩子。
醒來後這幾日她一直在等著孟挽,如今人說沒就沒,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正猶豫要不要去找白太後,借些人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轉過身,卻見晏二夫人跟前的老嬷嬷,腳底生風般朝她疾步而來,迎面就道:“少奶奶,趕緊回吧,世子爺回來了。”
誰?
腦子裏的茫然和怒意還未完全退去,白明霁一時沒反應過來,脫口而出,“哪個世子爺。”
傳話的嬷嬷一愣,僵硬地笑了笑,“少奶奶這話問的,還能有哪個世子爺,您的夫君,晏世子回來了。”
她的夫君。
永甯侯府世子,晏長陵。
回來了?
一個本該半年後死在戰場的人?白明霁思緒徹底亂了,訝然地盯著嬷嬷。
嬷嬷見她這反應頓時一噎,先前聽二夫人背地裏數落,說她莫不是她忘記自己已嫁了人,如今瞧來,還真給忘記了。
走過去一把攙扶住她胳膊,待扶上馬車後,便立在窗前板著臉道:“有幾句話,少奶奶或許不愛聽,老婆子今日也非得說了,少奶奶已是出嫁的人了,別動不動就往娘家跑,這不得體,先前便也罷了,如今世子爺已回來,還望少奶奶往後謹記自己的身份,論起規矩,少奶奶還是京城姑娘們的楷模呢......”
這話多少帶著揶揄。
上輩子在晏家住了一年,白明霁參加過的家宴,一個巴掌都能數過來。
夫君不在,她頂多算半個晏家媳婦。
與晏家人的相處,主打一個井水不犯河水。
至于不相幹的人,她懶得費神。
放在往日,盡管晏家有人對她這番目中無人的行爲看不順眼,但奈何理虧,嫁過來就讓人家守了空房,加之她身後的那位白太後,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如今世子回來了,總算有人治她了。
懷揣著這般心思,嬷嬷今兒要叮囑的話格外多,到了晏家,等白明霁從馬車上一下來,張嬷嬷便跟在她身後繼續說教,“院子裏的奴才,原本是伺候世子的人,縱然一時不合少奶奶心意,好歹也是十來年的老人了,少奶奶不該將人攆了。”
言下之意,如今人回來了,我瞧你怎麽交差。
見白明霁一句不吭,張嬷嬷心中暗自感慨,這人啊,萬不能太傲,總有栽跟頭的時候。
想起先前她一副天靈蓋上長眼睛的樣,如今倒是巴不得這關頭上鬧出個事情來,好讓世子瞧瞧,娶的是尊什麽樣的菩薩。
盼什麽來什麽,兩人的腳步剛上竹院長廊,便聽見裏面傳來了一陣吵鬧聲。
隱約能聽出是白明霁跟前的金秋姑姑。
張嬷嬷心頭一跳,這也太靈了,眼睛裏生了光,嘴裏卻裝模作樣地道:“有什麽天大事還值得吵一番,也不瞧瞧今兒是什麽日子。”
腳步不覺走到了白明霁前頭,到了人群背後,雙手往胸前一疊呵斥道:“這又是怎麽了?”
二夫人剛派過來的姚姑姑被攔在門外,也不知道金秋說了什麽,氣得她臉頰發紅,回頭見是張嬷嬷,這下有了底氣,聲音也大了,“嬷嬷來得正好,您給評評理,今兒世子爺回來,二夫人好心讓咱們的人過來幫忙打掃,誰料這門前多了一道門神,把咱們攔在外,不讓進了。”
張嬷嬷聽明白了。
什麽樣的主子養什麽樣的奴才,又是老一套。
上回被攆的幾個奴才告到二夫人跟前,二夫人好心好意找上門來調解,白氏以頭疼要歇息爲由,讓二夫人吃了個閉門羹。
張嬷嬷把目光看向了金秋姑姑,也不指望她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放人進去。
果然金秋姑姑道:“別說是張嬷嬷,今日就算二夫人來了,這趕出去的奴才,豈有再請回來的道理。”
說的是姚姑姑身後的一位丫鬟。
那丫鬟原本是屋裏伺候世子爺茶水的人,名喚玉珠,人是機靈,但話太多,白明霁喜歡清淨,便把她調去了後廚。
後廚婆子多,適合她唠嗑。
但她不願意,跪在白明霁跟前哭,問她自己做錯了什麽,與其被她這般羞辱,不如放她走。
本以爲她是世子的人,白明霁不敢處置,誰知白明霁竟成全她,當場把牙行的人叫了過來,玉珠嚇得大哭求饒,二夫人聽到消息把人攔住,暫且收在了自己屋裏。
今日八成是聽說了世子回來的消息,打了要來訴說冤屈的主意。
金秋姑姑死活不放人,幾人便端著水盆,拿著掃帚堵在門口。
張嬷嬷一聽金秋姑姑如此說,轉過身便對剛下長廊的白明霁,嘴角扯出個無奈的笑容來,“奴才無能,還是少奶奶處理吧。”
衆人這才瞧見剛下穿堂的白明霁。
個個臉色微變,垂目往後退。
衆所皆知,這位少奶奶不好惹,旁的主子動了怒,摔個東西罵上一頓便也罷了,她不是,但凡被她抓到錯處,那便甭想再呆在院子裏了,一次機會也不會給。
玉珠不久前才領教過。
鼓起勇氣擡頭,便見白明霁正冷眼盯住她,“你還有話說?”
觸到她目光,玉珠心頭便是一跳,脖子又縮了回去。
換做往日她確實不敢再來,今日不同,有人替他撐腰,硬著頭皮沖出去跪在了院子中央,擺出一副要升堂伸冤的架勢,同她叫囂:“奴婢不服。”
金秋姑姑沒見過這等子死皮賴臉的,倒吸一口涼氣,“這會子天晴,能跪了。”
然而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她能說得過姚姑姑,卻沒玉珠的口才,反倒被玉珠蛇纏棍子纏上了,“奴婢知道姑姑讀過書,說起話來走路繞小道,總要拐個彎,殊不知這墨水喝到了肚子裏,五髒也被染了色,我能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是我技不如人,沒有姑姑一根筷子揀花生米的本事,這才惹了少奶奶不快,要來發落奴婢。”
一頓夾槍帶炮,說金秋姑姑挑撥了。
有了上回的教訓,玉珠明白當奴才的萬不能同主子對著幹,這回學聰明了,把矛頭對准了白明霁的陪嫁姑姑身上。
“你!”
金秋姑姑氣結。
當初就因爲這點,娘子才容不得她。
擡眸看向白明霁,見其一身占了雨霧,沒功夫同她掰扯,“娘子先回屋更衣,她願意跪著就跪著吧。”
若是上輩子,白明霁或許會殺雞儆猴。
重生回來,她背負著血海深仇,定不是來管這些雞毛蒜皮之事,這屋子的主人既然已回來了,該如何處置隨他。
正要進屋,那玉珠竟不依不饒了,大聲哭喊起來,“奴婢跪著無妨,只等少奶奶消氣,今兒就算是跪死,奴婢也認,奴婢生是竹院的人,死是竹院的魂。”
最後兩句擡高了聲音,竟叫得比烈婦還貞。
白明霁轉過身,倒好奇她哪裏來的底氣,一道清朗的聲音突然從對面廊下的卷簾內傳來,“誰要死了?”
驚蟄雨水纏綿,檐下裝上了一排厚重竹篾卷簾,擋了雨霧也擋住了視線,待細風過,吹得簾子起伏,裏面那道影影綽綽的身影在一衆人的注視下快步走了出來。
是位年輕公子,青色劍袖圓領袍,手握一把銀槍,從踏跺潇灑踱步而下,舉手投足一股少年將士的幹練,五官卻不似武將的粗礦,白皙精致,唇角的一抹笑彷佛天生。
有些熟悉。
白明霁愣了愣,不就是打馬濺了嶽梁一身泥水的那人。
沒等她反應,跪在院子裏的玉珠如同見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梨花帶雨般地哭訴,“世子爺,求世子爺替奴婢做主......”
白明霁又怔了怔。
實則她並沒見過晏長陵,新婚當夜她頭上的蓋頭剛被掀開,門外便來了宮人,等她擡頭時,只看到了一個匆匆離去的背影。
邊沙之地,竟能養出這樣的細皮嫩肉。
倒不是小白臉。
少年的陽剛之氣洋溢在了臉上。
四目交彙還能感受到他視線裏散出來的灼熱,一雙黑眸澄明深邃,似是在星海裏浸泡過,含著笑漫不經心從一衆人身上掃過,略過她時突然一頓,似乎城門口的那一眼,也沒將她認出來,是以,又在她身上多停留了一陣。
她一身妝花金線绫羅,氣勢自與下人不同,此時能站在他房門前,什麽身份不言而喻。
晏長陵自然也看了出來。
新婚夜記不清有沒有見過白氏,似是瞧過,又沒瞧過,印象模糊,即便是前世最後一眼,她臉上沾了鮮血,也沒看真切。
這回倒是瞧仔細了。
肩上披著的還是適才在城門口見到的那件披風,肩膀有些消瘦,顯得身姿格外婀娜窈窕,頭上發絲被雨水打濕,沾了雲煙。
時下京城文人頗多,但凡長相過得去的小娘子,都被稱爲美人兒,大多美人兒在于皮相和點綴,瞧過之後則了無痕,記不清長相,跟前的姑娘不同,本身就是一塊美玉,不需要過分的雕琢,沉靜中流露出來的清雅從容,倒讓人過目不忘。
確定自己之前是沒見過。
隔了兩世頭一回相見,比起城門前見到的那一幕,對她上輩子那般淒慘的結局更有感觸,含笑對她點了下頭。
對方俯身還了他一禮。
耳邊的嗚咽哭聲還在繼續,晏長陵這才垂目看向腳邊跪著的那位奴婢,問道:“你哭什麽?”
嗓音偏低沉,聽進人耳朵,像是被一汪暖暖的泉水包裹,玉珠愈發委屈了,什麽也顧不上了,像是向家長告狀的孩子,巴巴地等著主子替自己做主,“世子爺,少奶奶要攆奴婢走,還打發了牙子要將奴婢賣了......”
只要跟過晏長陵的人,誰都知道他護短。
晏長陵如她所願地往白明霁的位置看去。
白明霁面色坦然,也沒反駁半句。
晏長陵又回過頭問玉珠:“何故攆你?”
“奴婢,奴婢冤枉......”
“什麽冤屈,說來聽聽。”院子裏有一方石桌,之前他喜歡在這裏與客人下棋,如今一場雨,上面鋪滿了落葉,橫豎身上濕了,沒去顧上面的水漬,往石凳上一坐,手中銀槍靠桌豎著。
張嬷嬷心頭激動,忙同姚姑姑遞了個眼色。
姚姑姑會意,這是要清理門戶了,忙領著帶來的丫鬟出了院子,跨出門檻後,話裏有話地道:“今日青天老爺在,誰還能有冤屈?”
在竹院有冤屈的,不就那幾個被白明霁趕出來的奴才。
深院裏圍牆一圍,四四方方也算得上一座小城,有點熱鬧,誰也不想錯過,趕緊找人傳話。
院子內玉珠也意識到自己今日占了上風,人跪在晏長陵跟前,妙語連珠,“奴婢也不知到底哪裏得罪了少奶奶,思來想去,估摸著許是世子爺那套茶具少奶奶想換,奴婢一時糊塗,護了兩嘴......”
金秋姑姑喉嚨裏‘嘶’出一聲,“你那是護了兩嘴,十嘴都算少的了,你是如何說的你忘了?你......”
“奴婢伺候了世子爺五年。”玉珠一聲打斷她,膝行幾步,拖著哭腔道:“世子爺人不在,奴婢想著屋裏總得留點之前的東西,好有個念想,少奶奶不愛聽,還要把奴婢給賣了,若非二夫人那日攔了下來,奴婢,奴婢早就,奴婢不活了......”說著要起身去撞樹,被邊上的婆子拉住,衆人七嘴八舌相勸,好不熱鬧。
很久沒這麽被吵過了,白明霁眼皮子兩跳,頭偏向一邊,正想回避,前面石凳上坐著的人,忽然回頭,朝她望來,“不過來聽?”
白明霁擡頭時,他已收回視線,從袖筒內掏出了塊幹爽的帕子,遞給旁邊的侍衛,“水擦幹,讓少奶奶坐。”
確定他喚的是自己,白明霁走了過去。
見她乖乖地坐在世子爺身旁,鬧騰的玉珠終于安靜了下來,擺出一副不是自己非要找事,而是被逼無奈的委屈狀,“若是奴婢一人,奴婢倒也覺得是自個兒不是,可院子裏的人少奶奶換了大半,奴婢著實,著實想不明白......”
晏長陵頗有耐心地聽她說,“還有誰冤屈了?”
話音一落,外面一串倉促的腳步聲回應了他,三五個小厮接二連三同玉珠跪成了一團,齊聲喊冤,“世子爺,求世子爺替小的做主......”
白明霁對這幾人有點印象。
半夜出去賭錢,被她回來撞上,第二日一早便讓他們收拾東西滾蛋。
冤,哪裏來的冤?
但人不是他的,晏長陵要想叫回來,她沒意見,“我......”
幾人卻沒給她發話的機會,“世子爺,奴才伺候世子爺十年了,從未有過差池......”
“小的替世子爺養了阿俊六年,也不知奴才走後,旁人有沒有好好待它,奴才對不住世子爺......”
“世子爺......”
好吵。
白明霁討厭哄哄鬧鬧,一吵頭便疼,指甲不自覺想去扣東西。
“奴才做得不好,願意受罰,求世子爺不要趕奴才走......”
“求世子爺.....”
滿院子的喊冤,一聲賽過一聲,白明霁都快把膝上的一縷金線扣出來了。
“世子爺......”
眉心突突兩跳,白明霁忍無可忍,壓在心口的怒火說爆就爆,手邊上正好有個趁手的家夥事,抄起擱在石桌旁的那把銀槍,起身,脫手一扔,“砰——”銀槍穩穩當當地插進了幾人身後的榕樹枝幹上,憋著的一口氣她全使了出來,力道不小,銀槍的尾巴“呼呼——”一陣搖晃。
連著落了幾日的雨,樹枝上積滿了水,嘩啦啦落下來,跪下的幾人被淋了個落湯雞。
可算都閉嘴了。
一套動作行雲流水,白明霁也終于吐出了那口氣,“吵什麽吵!”
耳邊死寂般的安靜。
怒氣慢慢散去,回過神待看清對面樹上定著的是什麽東西後,白明霁心下一涼。
她聽說過那杆銀槍的來曆,乃皇帝當年登基時,親自所賜。
十六歲時便伴著他勇闖沙場,幾年下來,飲血無數。
眼眸輕輕往邊上轉去,余光瞥見一道目光正盯著自己,便也沒那個必要再去來個對視。
誰也沒說話,等著她自己收場。
扔了人家的槍,總得撿回來。
白明霁一邊往樹下走,一邊義正言辭地道:“再吵就賣了!”
可扔的時候沒掌握好高度。
伸手夠是夠到了,但使不上力,一下沒拔動。
又使勁,還是沒動。
再拔下來,只會更難看。
白明霁迫使自己回頭,迎上對面那道黑沉沉的目光,平靜地道:“是我爲難他們嗎?當奴才得有當奴才的樣,主子回來,不伺候更衣,反而來伸冤,這算哪門子的忠心。”
腳尖一挪,又道:“我去替世子叫水。”